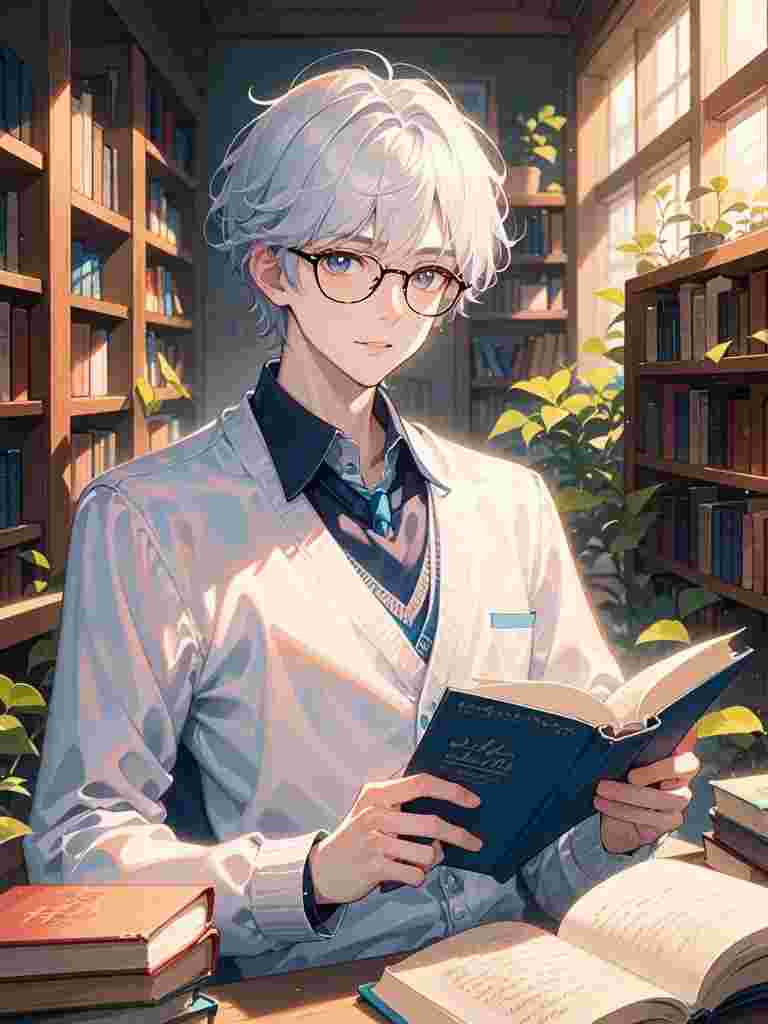行。
他撑不了三次。
果然,第三次冲关时,他身体一僵,喉头滚了下,又咳出一大口血。
可他抬手抹去,继续。
我转身离开。
他知道自宫是开始,却不知道——死,才是终点。
回到房中,我磨剑。
断江刃口崩过三处,我一寸寸磨平。
门外传来脚步声,很轻,停在我门口。
我没抬头。
门没开,脚步又退了。
我停下磨剑的手,剑刃映着烛光,冷得像冰。
我知道是谁。
她来过,又走了。
或许她想问那功法有没有问题,或许她看见了裴无咎的血。
可她终究没进来。
因为她心里,早已选好了答案。
我收剑入鞘,吹灭灯。
黑暗中,剑穗垂在身侧,一动不动。
屋外,风卷起一片枯叶,砸在窗纸上,发出轻响。
我闭上眼。
自宫……才是开始。
3天光刚透,窗纸由黑转灰,我仍坐在床沿,断江横在膝上,剑穗垂地,一动不动。
昨夜风停了,枯叶贴在窗上,纹丝未动。
我没合眼,也不觉得累。
起身时,青衫已冷,袖口沾着昨夜磨剑时蹭上的铁屑。
我抖了抖衣,推门出去。
演武场已有弟子列队,晨雾未散,人影晃动。
裴无咎站在场心,黑袍裹身,脸色比雪还白。
他练的是基础剑式,可每一剑都带出风声,剑尖震颤,竟有内门高阶的力道。
几个外门弟子低声议论。
“裴师兄三日突飞猛进,莫非打通了玄关?”
“听说他昨夜练到子时,回来时嘴角带血,还在笑。”
我站在场边,不动声色。
他的步伐虚浮,出剑时肩头微颤,那是气血逆行的征兆。
真气不走正脉,反冲奇经,短时能强,长久必溃。
他现在像一壶烧裂的铁锅,水还在喷,锅底已漏。
沈清漪来了。
她没穿厚衣,披着素色披风,手里捧着一方布巾,站在裴无咎身后半步。
他收剑,喘息,她立刻上前,替他拭去额角冷汗。
指尖擦过他眉骨,他抬眼,两人对视一瞬。
她没躲。
我转身离开。
回到居所,我关上门,从枕下取出一张废纸,摊在案上。
提笔,默写《玄阴诀》真本前三章。
字迹工整,一句不差。
养气三年,通脉循序,无捷径可走。
再取另一张纸,写下我昨夜给裴无咎的假本。
<首页八字:“欲练此功,必先自宫。”
江湖旧闻,常有疯子信以为

妻子抢我剑谱给师弟,他挥刀自宫小说
推荐指数:10分
热门小说《妻子抢我剑谱给师弟,他挥刀自宫小说》是作者“桃子快到怀里来”倾心创作,一部非常好看的小说。这本小说的主角是萧砚沈清漪,情节引人入胜,非常推荐。主要讲的是:我叫萧砚。青城派外门弟子。靠一把断江剑,拼出前程。娶了掌门独女沈清漪。本以为是人生巅峰。结果她心里一直装着小师弟裴无咎。那小子一张小白脸,嘴甜手不干净。她护他,比护我还上心。直到那天,她持剑对准我。“把秘籍交出来。”我笑了。递上我亲手改过的《玄阴诀》。第一句:“欲练此功,必先自宫。”她信了。我心死了......
第6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