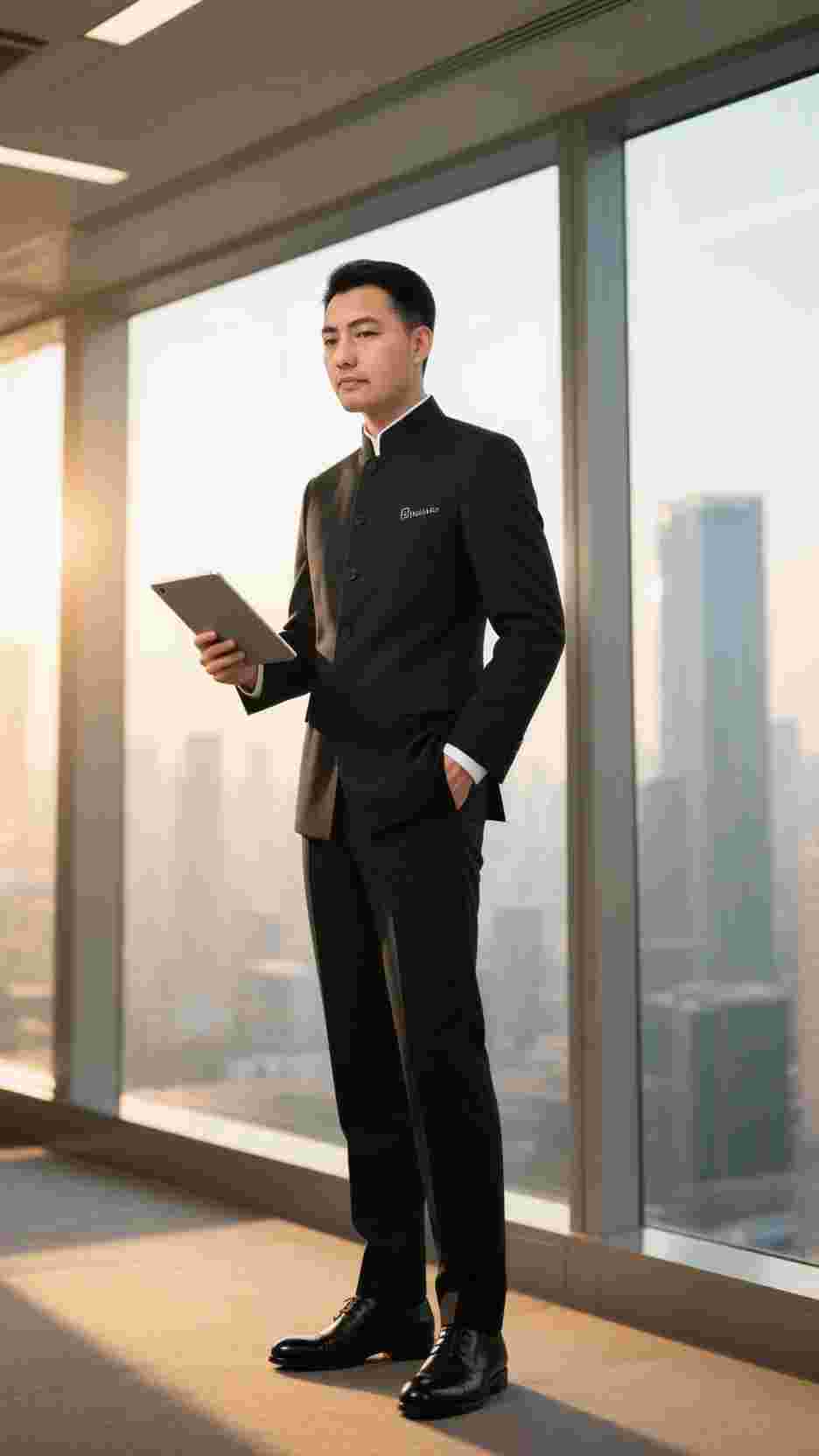是红肿的。
母亲看见,什么也没问,只是默默地在早餐时给他多煎了一个荷包蛋——这是他小时候心情不好时,父亲惯用的安慰方式。
饭后,母亲开始整理父亲的遗物。
林宴在一旁帮忙。
父亲的东西很少,衣服大多是穿了多年的旧衣,叠得整整齐齐。
书桌上除了几本工具书,几乎没有其他杂物。
抽屉里放着一些票据、证件,还有一个小铁盒。
母亲拿起那个锈迹斑斑的小铁盒,打开。
里面并没有什么贵重物品,只有几枚褪色的奖章(父亲年轻时厂里劳动竞赛得的)、几张老旧的照片、一本更小更旧的笔记本,以及……一沓汇款单的回执。
林宴拿起那沓回执,一眼看去,心跳骤然停了一拍。
汇款人全是林天明。
收款人……是林宴。
时间从他刚上大学开始,几乎每月一张,金额从一开始的三五百,到他工作后变成一千、两千……最近的一张,日期就在三个月前,金额五千。
汇款附言栏里,永远只有简短的两个字:“安心。”
他猛地抬头看向母亲。
母亲避开了他的目光,声音低沉而沙哑:“你爸他……总觉得你一个人在外面打拼不容易,大城市花销大。
他怕你钱不够用,又不好面子,不肯开口问家里要,就偷偷给你寄。
我说直接转账,他非说不一样,说这是‘实在的钱’……”母亲的声音哽咽了,“他总觉得给你的不够多、不够好……”林宴看着那些泛黄的、字迹却依旧清晰的回执,只觉得它们像一块块烧红的烙铁,烫得他手心发疼,一直疼到心里去。
他想起大学时,账户里时不时多出的“生活费”,他总以为是母亲打的。
想起工作后,父亲每次打电话来,最后总会硬邦邦地加一句“缺钱就说”,他当时还觉得父亲小瞧了他。
原来,父亲一直在用这种最笨拙、最原始的方式,默默地、持续地,为他输送着支持。
而他,竟然从未察觉。
他以为自己早已独立,早已不再需要父亲的庇护。
却不知,在父亲眼里,他永远都是那个需要被照顾、被惦记的孩子。
父亲沉默的爱,如空气般无处不在,却又被他轻易地忽略至今。
林宴蹲下身,将额头抵在冰冷的抽屉边缘,肩膀无法抑制地颤抖起来。
母亲的手轻轻

时光深处的无声告白后续+完结
推荐指数:10分
由小编给各位带来小说《时光深处的无声告白后续+完结》,不少小伙伴都非常喜欢这部小说,下面就给各位介绍一下。简介:医院的消毒水气味钻进鼻腔,混合着某种若有若无的衰败气息。林宴站在病房门口,手搭在冰凉的金属门把上,竟有些不敢推开。三天前,他还在另一个城市为了一份合同拼命奔波,接到母亲电话时,他正对着客户侃侃而谈。母亲的声音隔着电波,带着一种刻意压抑后的平静:“小宴,你爸……查出来了,不太好。是癌,晚期。医生说他最......
第8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