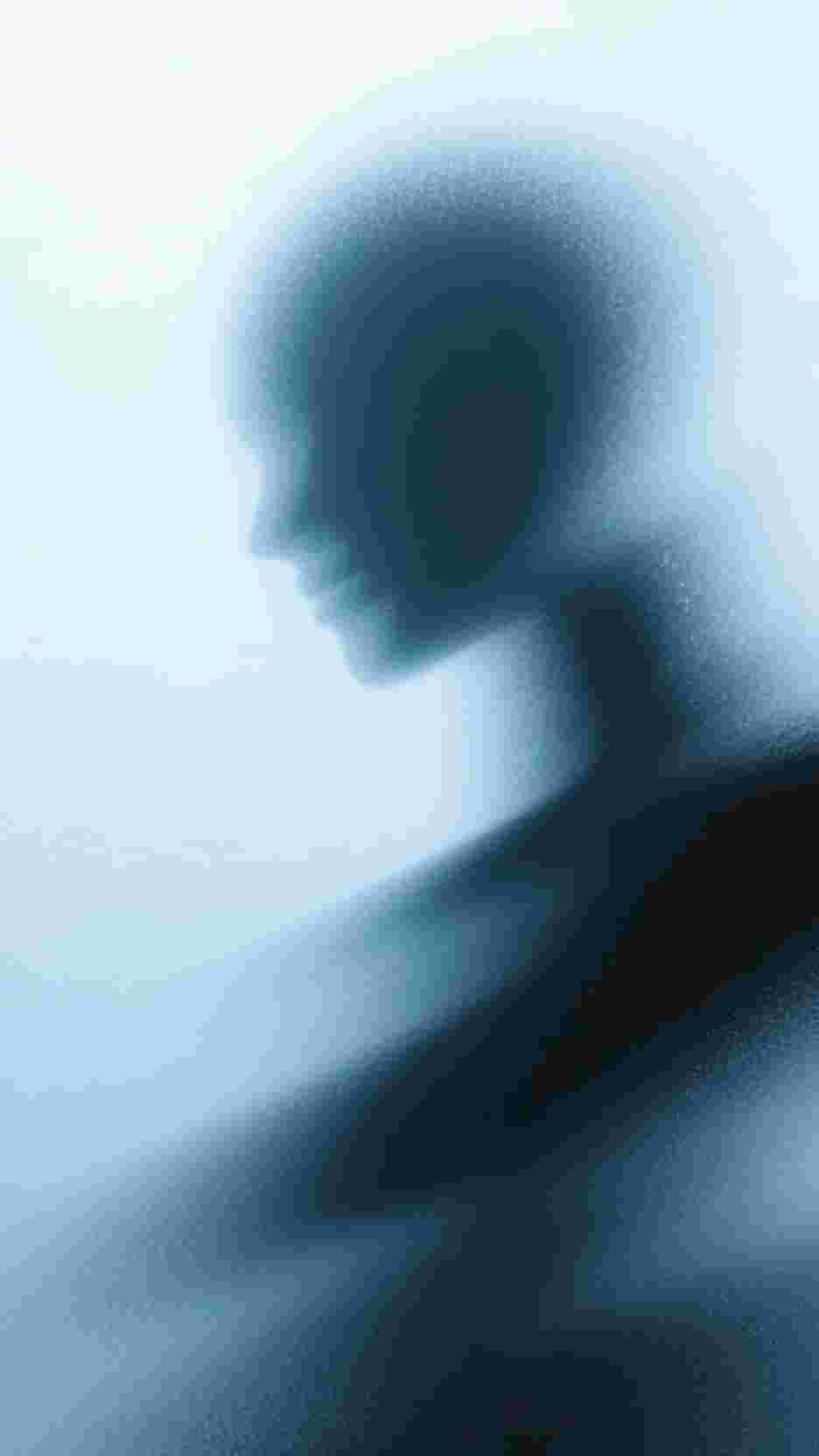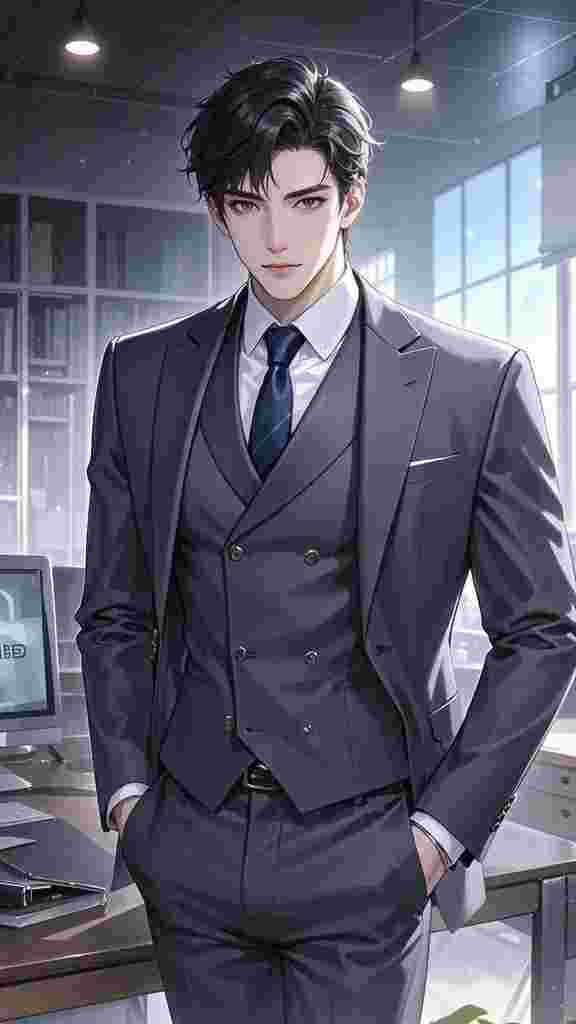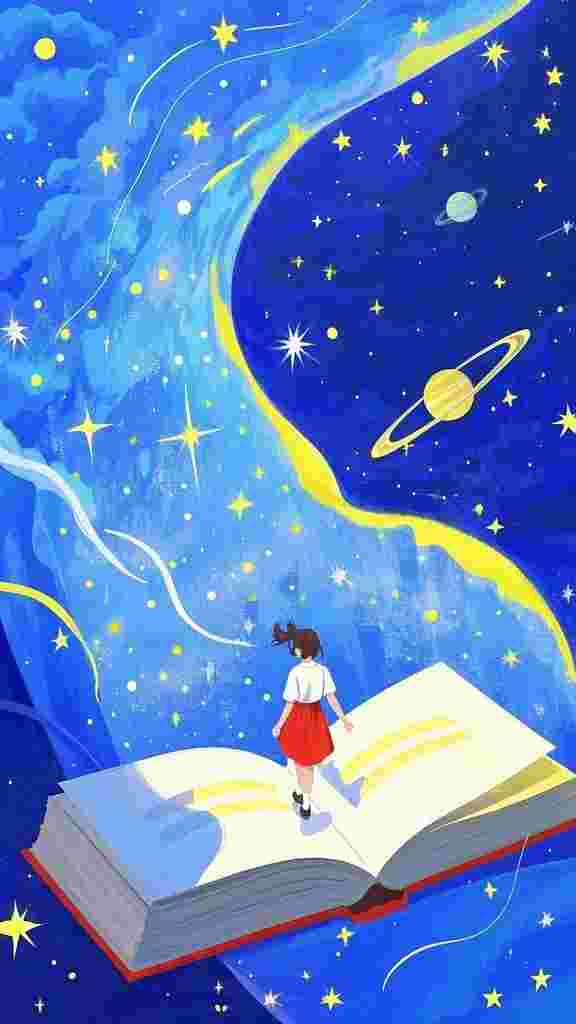个可能永远找不到她的沈知寒。
她开始重新誊写信件内容,凭着记忆和自己手抄的版本,尽可能还原当年的通信。
每誊完一封信,她就会在后面添加一些注释,说明当时的实际情况和她的真实感受。
“...你问我最喜欢伦敦的哪个季节,我说是春天,其实我从未去过伦敦。
那天上海下着春雨,我在窗口看着雨滴从梧桐树叶上滑落,想着如果你知道我在撒谎,会不会再也不理我了......你说令堂又做了太多的青团,其实我知道那是你特地买的。
谢谢你小心翼翼地维护我的自尊,那时的我太过年轻骄傲,不懂得坦诚有时比自尊更珍贵...”2005年,她完成了最后一封信的誊写和注释。
82岁的她将全部信件重新整理好,放入那个檀木匣子中,对女儿说:“如果我走了,把这个盒子交给苏晚。
告诉她,这里有一个未完的故事,如果有可能,请她继续讲下去。”
同年冬天,林薇如安详离世,床头放着那本《雪莱诗选》,扉页上多了两行字:“此情可待成追忆,只是当时已惘然。
——给知寒,但愿来生再见。”
第七章 伦敦寻踪苏晚放下最后一封信,窗外已经晨光熹微。
她一夜未眠,读完了祖母的全部信件和注释,仿佛经历了那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深情与遗憾。
她洗了个澡,煮了杯浓咖啡,然后做出一个决定:她要找到沈知寒,或者他的后人,完成祖母的遗愿。
第一个线索是沈知寒最后留下的香港地址。
苏晚通过网络搜索发现,那个地址所在的区域已经在五十年代重新开发,现在的建筑与当年完全不同。
她尝试联系香港的档案机构,查询1947-1948年间的入境记录,但被告知那个时期的许多档案已经在一次火灾中损毁。
第二条线索是复旦大学。
苏晚给学校档案馆发邮件,查询1946-1947年间在校任教的名叫沈知寒的英国文学讲师。
一周后,她收到回复:确有此人,但档案资料很少,只有一份教职工名册上的记录,注明他于1947年6月离职,原因不详。
回复中还附有一张模糊的黑白照片:1947年复旦大学教职工合影。
苏晚放大图片,在第二排右侧找

跨越半个世纪的爱苏晚雪莱:全文+结局+番外
推荐指数:10分
热门小说《跨越半个世纪的爱苏晚雪莱:全文+结局+番外》是作者“青龙凡泽”倾心创作,一部非常好看的小说。这本小说的主角是苏晚雪莱,情节引人入胜,非常推荐。主要讲的是:楔子苏晚整理祖母遗物时,发现一个褪色的檀木匣,里面整齐叠放着七十多封信件,最上面是一张1947年的旧报纸,头版刊登着一则寻人启事:“寻找在图书馆借《雪莱诗选》的姑娘。周三下午三点,和平咖啡馆等你。——沈”她翻开最上面一封信,泛黄的信纸上是一手漂亮的钢笔字:“致不知名的姑娘,今天在图书馆,我看见你坐在......
第11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