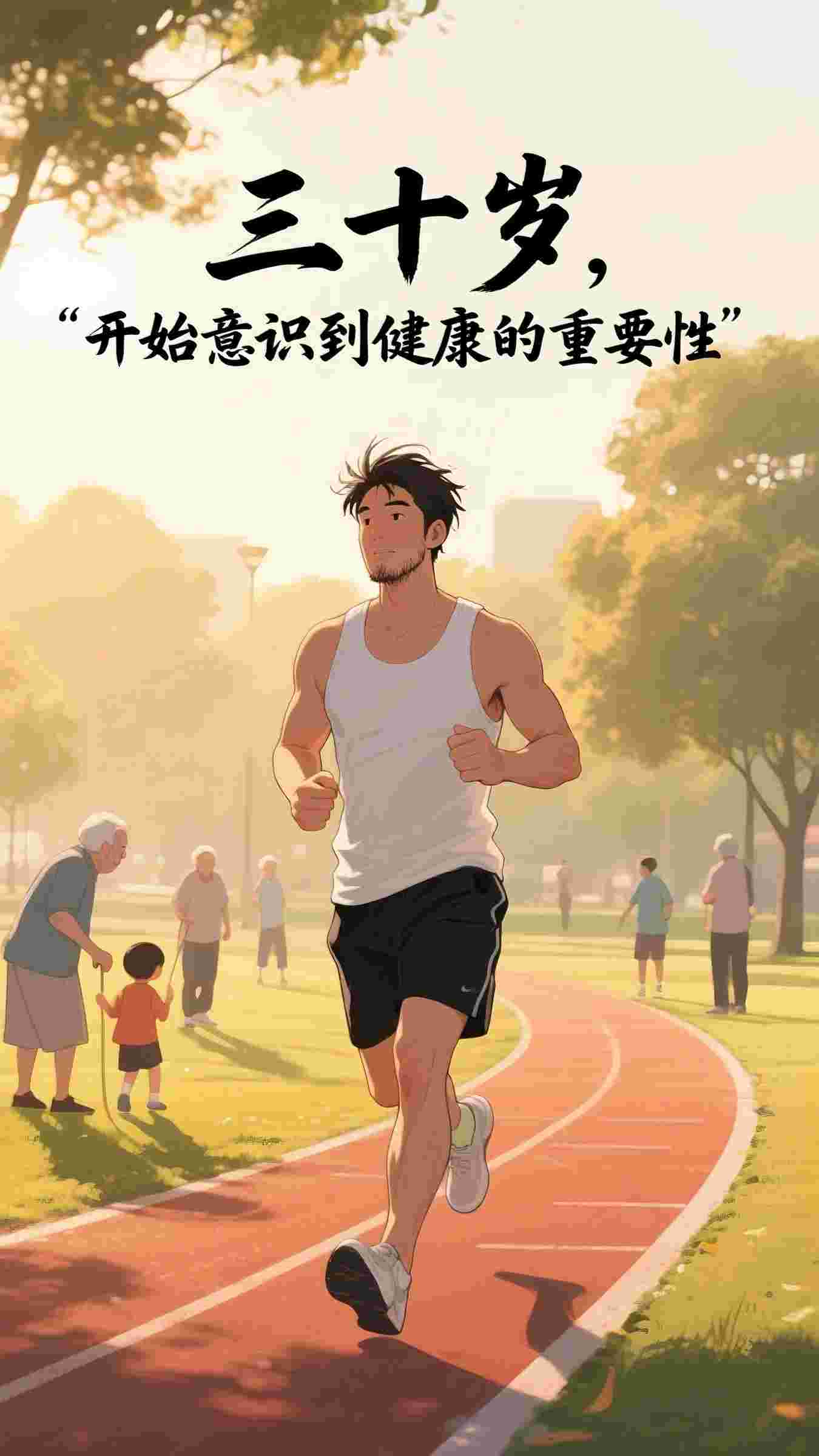如今见她要和离,又忙不迭将中馈交给她示好。
以为她傻?
她若接下中馈,非但不能和离,以后陪嫁更是得理所当然为他们周家填窟窿,被他们一家人蚕食干净。
她平静回答:“婆婆年富力强,春秋正盛,打理中馈一向好好的,交给妾身,于理不合。妾身也没这个能力。”
梅氏忙道:“你别谦虚了,你娘一个妇道人家都能将偌大的家业管得井井有条,有其母必有其女。你自然不会差到哪里去。”
苏盈皎仍推辞:“妾身比不上娘,才能不足,不可领此重担。”
梅氏见她死活不肯退让,脸色青了。
苏盈皎故意气她:“若婆婆没有其他事,妾身便先回去了,陪嫁物事太多,还需要花时辰整理。”
梅氏叫她还是要和离,脸色更难看了。
周相宜见母亲低三下四讨好半天还是热脸贴冷屁股,再憋不住了,一拍桌子:
“苏氏,母亲好意留你,你还给脸不要脸了?”
苏盈皎步子一驻,回头冷幽幽看向周相宜。
这目光看得周相宜一个哆嗦。
“我若真的脸皮够厚,何止带走全部嫁妆?连你周家原先用我的钱银,我都得让你们一一吐出来。”
周相宜脸色冷了。
梅氏更是青了脸色。
母女俩气得哆嗦,却只能眼睁睁看着苏盈皎转身离开。
——
这天应付完梅氏后,接下来的两天,总算清净一些。
清晨,苏盈皎刚用完早膳没多久,洛州来照顾她的陈妈妈疾步进来了。
她只当是来汇报老太太的近况。
却见陈妈妈一脸汗,神色紧张,将一封信递过来:
“娘子,丁管家从洛州送信来了。”
苏盈皎心里咯噔,有不好的预感。
自打来了京城,苏家便由老丁打理。
老丁是香袭的叔叔,跟了母亲几十年,可谓是徐氏的左右手,忠心耿耿,做事极有分寸,将苏宅打理得井井有条。
徐氏去世,她远嫁京城后,家中向来无事。
老丁也从没来过信。
她拆开信封一看,脸色变了。
徐氏去世后,根据她的遗言,单独葬于洛州城外的墓园。
当时还引得不少人非议。
妇人死后应该是与夫婿合葬或葬在夫家祖坟,哪有单独落葬的道理?
徐氏只说丈夫客死异乡,尸骨无存,只有衣冠冢,夫家人丁凋落,更无往来,所以坚持一人独葬。
丁管家说,最近洛州忽然来了一帮土豪劣绅,到处征地,说是为朝廷兴修牧场,刚好看中了徐氏的墓园,竟让苏家将徐氏的墓迁去别处,要占用墓园那块地。
丁管家自然不答应,可那群人见苏家家主已逝,唯一的独女远嫁,宅中无人管事,十分猖狂,下了通牒,若到了时辰,徐氏的墓还没迁走,就怪不得他们擅自动工,直接动土挖坟了。
香袭见苏盈皎脸色发沉,问:“娘子,苏宅是出什么事了?”
苏盈皎将这事说了。
香袭和陈妈妈气得直哆嗦:
“岂有此理!哪有为圈占土地,挖亡人坟地的道理!”
“简直没有天理!”
“娘子,千万不能让他们挖了夫人的墓,扰了夫人的清宁啊!”
苏盈皎说:“丁管家正与那帮人说理,闹还组织了一帮护院日日守在娘的墓地,防止那些人随意动土。可那些人捏着有朝廷印章的公文,怕是也护不了太久。”
“那怎么办?”香袭急了。
陈妈妈犹豫片刻,试探:“娘子现如今到底还是伯府儿媳,可要找伯爷和世子帮帮忙?”

重生当恶媳,绝嗣摄政王为她杀疯裴瞻苏盈皎前文+后续
推荐指数:10分
古代言情《重生当恶媳,绝嗣摄政王为她杀疯裴瞻苏盈皎前文+后续》是作者““月小兽”诚意出品的一部燃情之作,裴瞻苏盈皎两位主角之间虐恋情深的爱情故事值得细细品读,主要讲述的是:【夺人妻 强取豪夺 虐渣打脸 甜宠爽】前世,身为穿越二代的富商女儿苏盈皎与被流放地方的伯府世子成婚,用家产帮夫家重回京城。嫁入伯府后,她方知夫婿早有白月光。夫婿和白月光吃了她的绝户,用她的嫁妆吃香喝辣、生儿育女。白月光怕她的美貌迟早勾走世子,设计她被登徒子糟践,令世子对她弃若敝履。她的孩子被挖了心脏,给白月光有天生有心疾的孩儿当药引。她被关进别院,白月光放男人进去对她百般蹂躏致死。重生回被糟践那夜,苏盈皎敲碎登徒子的头,爬上了隔壁为母祈福的摄政王的床。*裴瞻摄政以来六亲不认,女色不沾身,不想有朝一日折在一个妇人身上。而这娇软似水的小妖精,还是崇阳伯的儿媳妇。虽知于理不合,他仍对这有夫之妇食髓知味,上了瘾,专横地不让她夫婿碰她分毫,恨不得将她软禁在自己床帏。就算担上个觊觎人妻、巧取豪夺的罪名也在所不辞。几个月后,苏盈皎孕吐。那男人……说好的绝嗣呢?夫婿让她交出嫁妆和娘家产业,安心养胎,切勿操劳。威严霸气的男人一袭蟒龙紫袍,踏入伯府:“本王的孩儿不劳尔等操心。”伯府阖府震惊!世子浑身绿光,气得晕死!公婆大骂:“你这荡妇,竟勾引外男——”随扈亮出锁链:“敢辱骂摄政王妃,丢进诏狱大刑伺候!”...
第46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