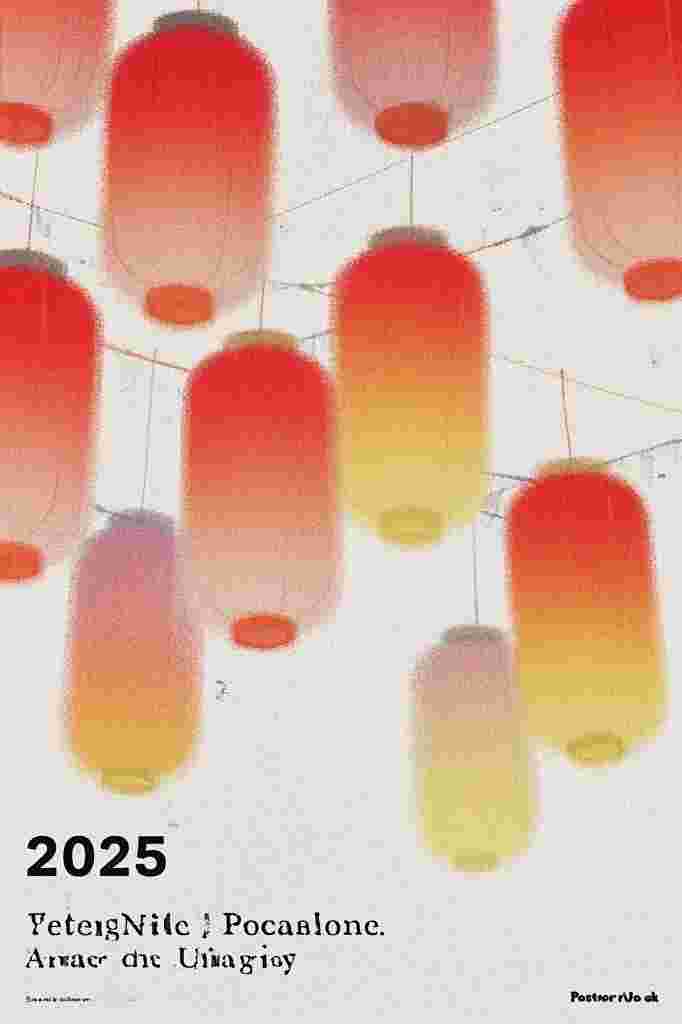叶心心的嘴唇动了动,却没发出任何声音。她只是静静地看着他,像在看一个与自己无关的陌生人。这眼神像根细针,精准地刺中他心底最烦躁的地方。
他猛地松开手,后退几步,胸口剧烈起伏着。壁炉里的火明明灭灭,映得他脸上的情绪忽明忽暗。他想发怒,想质问,想把她摇醒,可看着她那副失了魂的模样,所有的火气都像被雪浇过,只剩下无力的闷痛。
“你要绝食?”他的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妥协,“好,我不逼你吃。你想看雪?我让他们把木板拆了。你想回学校看看孩子?我带你去。”他甚至愿意退一步,只要她能开口说句话。
叶心心依旧沉默。她缓缓转回头,重新望向木板的缝隙。那里的天空不知何时暗了下来,雪粒打在木板上,发出沙沙的声响,像谁在低声絮语。
丹增看着她的背影,突然觉得一阵恐慌。他好像做错了什么,错得离谱。他以为把她困在身边,烧了她的念想,就能让她屈服,却没想过她会用这种近乎自毁的方式反抗。她的沉默像一张网,不仅困住了她自己,也缠住了他,让他动弹不得,只能眼睁睁看着她一点点枯萎。
他转身离开了房间,关门时的声响比平时轻了许多。走到回廊尽头,他对守在那里的侍女说:“把窗上的木板拆了。”
侍女愣了愣,连忙应声。次仁正好从外面进来,听到这话,低声劝道:“丹增,这样不妥吧?万一她……”
“拆了。”丹增打断他,声音冷得像冰,“让卓玛过来陪她。”
他知道自己在冒险。拆了木板,意味着给了她眺望外界的可能,给了她怀念陈阳的契机。可他别无选择,再这样下去,他怕这房间里的沉默会彻底吞噬她。
木板被拆下时,叶心心没有任何反应。直到一缕天光透过窗棂落在她脸上,她才缓缓眨了眨眼,像从一场漫长的梦里醒来。窗外的雪已经停了,菩提树枝桠上的积雪簌簌落下,在地上积起薄薄的一层,像撒了把碎盐。
卓玛端着一盆炭火走进来,看到叶心心望着窗外,小声说:“叶老师,外面冷,我给你端了盆火。”她把炭火盆放在叶心心脚边,火苗跳跃着,映得她辫梢的红绳格外鲜亮。
叶心心的目光落在卓玛身上,停留了很久,才缓缓抬起手,轻轻碰了碰她的辫梢。
卓玛的眼睛一下子亮了:“叶老师,你终于理我了!”她从袖袋里摸出颗水果糖,剥开糖纸递过去,“这是我阿爸从县城带回来的,橘子味的,你尝尝?”
叶心心没接,只是收回手,重新望向窗外。远处的雪山在暮色里泛着淡紫色的光,山涧的水声隐约传来,像谁在哼唱古老的歌谣。
卓玛把糖放在她手边,小声说:“丹增叔叔其实很担心你。昨天夜里,我看到他在你门外站了好久,手里还攥着你上次掉的发绳。”
叶心心的指尖动了动,却依旧没说话。
“他就是太犟了,”卓玛叹了口气,像个小大人,“他不知道怎么对人好,就只会用自己的方式。其实他……”
“卓玛。”叶心心突然开口,声音哑得像被砂纸磨过,这是三天来她第一次说话。
卓玛惊喜地抬起头:“哎!叶老师,我在!”
“能帮我倒杯水吗?”
“能!能!”卓玛连忙跑出去,很快就端着杯温水回来,小心翼翼地递到她手里。
叶心心接过水杯,指尖触到温热的杯壁,轻轻抿了一口。温水滑过干涩的喉咙,带来一丝微弱的暖意。她看着窗外渐渐沉下去的暮色,心里某个冰封的角落,似乎有了一丝松动。
她不会开口对丹增说话,不会吃他送来的食物,不会回应他的任何示好。这是她唯一能做的抵抗,是她在这座牢笼里,为自己保留的最后一点尊严。
但她会喝水,会听卓玛说话,会看着窗外的雪山。因为她知道,只有活着,才有等待的可能。陈阳的信虽然烧了,可那句“等我”,早已刻在了她的心底,像雪地里的种子,只要还有一丝温度,就终有破土而出的那天。
门外的丹增听到了房间里的对话,紧绷的神经终于松了些。他靠在廊柱上,听着卓玛叽叽喳喳的声音,听着叶心心偶尔发出的、极轻的回应,掌心的冷汗渐渐干了。
他知道这场无声的抵抗还远远没有结束。她的沉默是对他的惩罚,也是对他的提醒——有些东西,不是靠强硬就能得到的。
风卷着雪粒掠过回廊,带着雪山的寒意。丹增紧了紧藏袍的领口,目光落在那扇亮着灯的窗户上。灯光透过窗棂,在雪地上投下温暖的光斑,像朵倔强开放的格桑花。
他有的是耐心。他愿意等,等她开口,等她回头,等她明白,这世间除了陈阳那句遥远的“等我”,还有一个人,愿意用笨拙的方式,陪她度过每一个寒冷的冬夜。
只是他不知道,这场等待,会耗费多少时光,又会让两人都承受多少煎熬。"

她去支教,却撞上霸总硬核求爱叶心怡云桑结局+番外
推荐指数:10分
古代言情《她去支教,却撞上霸总硬核求爱》,主角分别是叶心怡云桑,作者“小妖姨”创作的,纯净无弹窗版阅读体验极佳,剧情简介如下:她满腔热血奔赴西藏支教,却一头撞进权势织就的牢笼。藏地雄鹰般的男人强势介入,以不容拒绝的姿态将她困在雪山深处。男友的退缩让她孤立无援,而他的步步紧逼更让她进退两难。原以为只是短暂的支教之旅,却成了无法逃脱的纠葛。她恨他的霸道,却又在日复一日的相处中滋生依赖。当温柔与压迫交织,自由与禁锢拉扯,她该如何挣脱这场高原困局?...
第48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