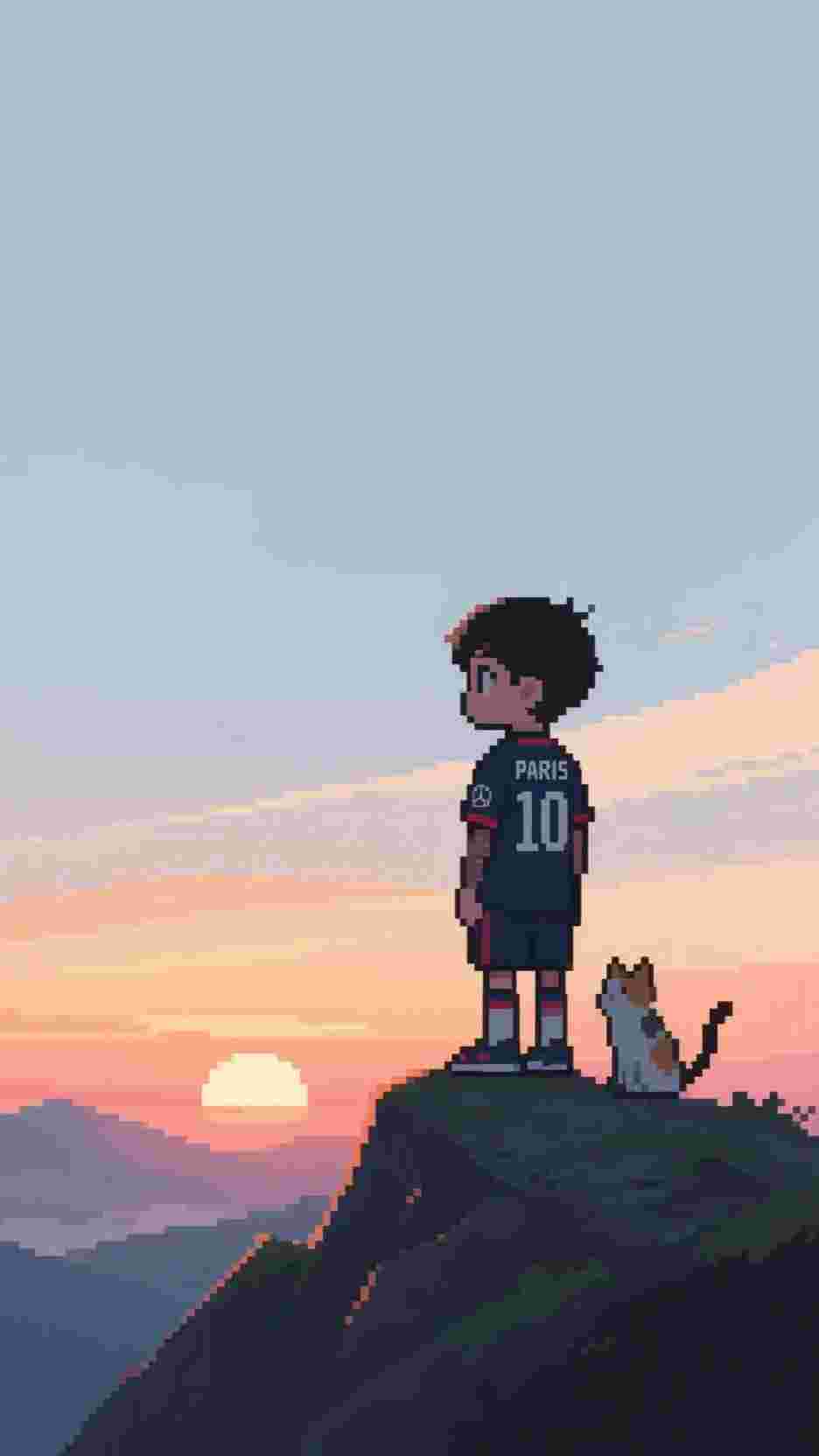冷地打在我脸上。
天桥下,只剩下阿海那变得清泉般悦耳的、带着惊惶余音的询问,在雨夜里回荡。
我瘫坐在湿冷的地上,指尖残留着诡异的灼热和一种空荡荡的虚弱感,望着阿海完全陌生的、被新生的清亮嗓音所笼罩的脸,巨大的困惑和一丝难以言喻的恐惧,像藤蔓一样紧紧缠绕住心脏。
那晚之后,我和阿海之间弥漫着一种诡异而尴尬的沉默。
他不再轻易开口唱歌,偶尔说话,那崭新清亮的声音总会让他自己和我都愣一下。
他看我的眼神变了,不再是看一个同样在街头挣扎的可怜虫,而是混杂着敬畏、感激和一种深切的困惑。
他不再邀请我一起唱歌,只是沉默地拨弄他的吉他,音符也显得心事重重。
雨夜天桥下的“奇迹”,却像投入死水潭的石子,涟漪缓慢却固执地扩散开来。
先是隔壁街区一个以唱戏曲为生的老头,据说年轻时嗓子极亮,后来坏了,只能靠放录音乞讨。
他不知从哪里听说了什么,在一个阴沉的午后,拄着拐棍,颤巍巍地摸到天桥下。
浑浊的眼睛在阿海和我身上逡巡,最后落在我身上,带着孤注一掷的哀求和卑微。
“姑娘……行行好……”他的声音像漏气的风箱,“他们说……你能……能治嗓子?”
我头皮发麻,下意识地想躲。
那晚指尖灼烧的剧痛和随之而来的虚脱感,刻骨铭心。
但看着老人浑浊眼睛里那点微弱却固执的亮光,看着他干枯的手死死抓着那根磨得发亮的拐杖,拒绝的话卡在喉咙里,怎么也说不出口。
阿海在一旁默默看着,眼神复杂。
“我……我不知道……”我声音抖得厉害。
老人却像抓住了最后的稻草,几乎要跪下:“求求你……试试……试试就好……”众目睽睽之下,我别无选择。
我深吸一口气,带着赴死般的决心,伸出微微颤抖的手,指尖轻轻碰触到老人布满褶皱的、冰冷的手腕皮肤。
轰!
比上次更猛烈的灼流瞬间炸开!
仿佛有滚烫的钢针顺着我的血管扎进心脏,再扎向四肢百骸!
眼前瞬间一片漆黑,金星乱舞。
我死死咬住下唇,尝到了腥甜的铁锈味。
剧烈的耳鸣中,我听到自己压抑不住的痛哼。
灼流退去后,我瘫软在地,冷汗瞬间浸透后背,胃

声音天使林默阿海:全文+结局+番外
推荐指数:10分
以现代言情为叙事背景的小说《声音天使林默阿海:全文+结局+番外》是很多网友在关注的一部言情佳作,“枕汐愈心”大大创作,林默阿海两位主人公之间的故事让人看后流连忘返,梗概:冰冷的雨水敲打着天桥的水泥顶棚,像无数细碎的鼓点,密集而冰冷。我缩在角落的阴影里,怀抱一把褪了漆的木吉他,廉价音箱在脚边发出嘶哑的电流噪音。面前的琴盒敞开着,里面零散躺着几张被雨水洇湿的纸币,还有几枚冰冷的硬币,寒酸得可怜。林默——我的名字,沉默的默,此刻像个无形的诅咒,沉沉压在舌尖。喉咙深处梗着某......
第3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