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群人的簇拥下走了进来。
他瘦了些,轮廓更加分明,穿着一身剪裁得体的深灰色西装,整个人散发着一种生人勿近的冷冽气场。
他的目光扫过全场,在看到我时,有片刻的停顿,随即像掠过一件无足轻重的摆设一样,自然地移开了。
整个会议,他都在和他的团队、和我们的馆长讨论,条理清晰,逻辑缜密,没有给我一个多余的眼神。
我坐在那里,像个透明人。
手里紧紧攥着笔,指甲掐进掌心,用疼痛来维持表面的镇定。
会议结束,众人陆续离开。
我整理着文件,磨蹭到最后。
他还在和助理交代着什么,声音低沉而有磁性,是我曾经在无数个深夜里听过的声音。
我深吸一口气,站起身,走到他面前。
“沈工。”
我用最客气、最疏离的称呼。
他抬起眼,目光平静地落在我脸上。
“江小姐,有事?”
那声“江小姐”,像一根针,精准地刺进我的心脏。
我准备了一路的开场白,瞬间忘得一干二净。
“关于展区的设计理念,我有些初步的想法,想和您单独聊聊。”
我听到自己用一种僵硬的、公事公办的语气说道。
他看了一眼手表。
“我的时间很紧。
具体事务,你可以和我的助理对接。”
说完,他便转身,没有丝毫的拖泥带水,留给我一个冷硬的背影。
我站在原地,看着他越走越远,直到消失在走廊尽头。
那一刻,我才清晰地认识到,我们之间,真的只剩下工作关系了。
那些曾经的温存与缱绻,都成了不可提及的过往。
.4 意外项目有条不紊地进行着。
我和沈青芜的交集,仅限于每周一次的项目例会,和偶尔在施工现场的偶遇。
我们之间,永远隔着一群人,隔着图纸和模型。
他对我,客气、礼貌,却也疏离得像隔着千山万水。
他会指出我方案里的不足,也会肯定我好的创意,但他的眼神,永远是专业而冷静的,不带一丝私人情绪。
我渐渐习惯了这种模式,把所有的心力都投入到工作中。
我熬夜修改方案,泡在施工现场跟进进度,用忙碌麻痹自己。
那天下午,天气预报说有雷阵雨。
我担心新建展区的一个天窗防水有问题,便独自一人去了还在施工中的大楼。
工人们大多已经下班,空旷的建筑工地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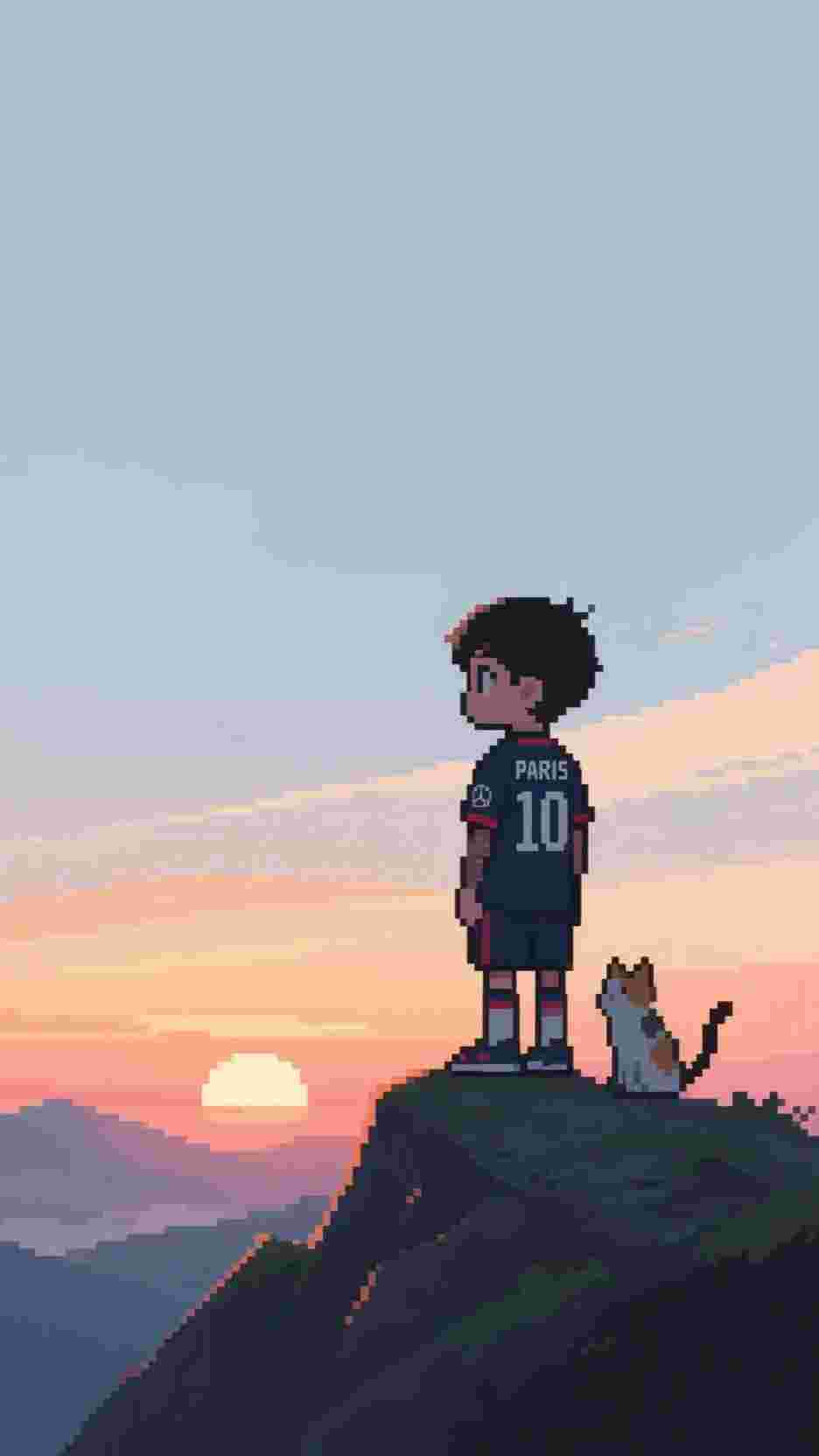
我掏空全部积蓄救弟弟,老公连夜提离婚沈青芜青芜全文
推荐指数:10分
《我掏空全部积蓄救弟弟,老公连夜提离婚沈青芜青芜全文》是由作者“我有一只墨笔”创作的火热小说。讲述了:1 裂痕空气里弥漫着一股灰尘和新墨水混合的味道。那张薄薄的A4纸,被沈青芜修长的手指推到我面前,边缘锋利得像能割开皮肤。“签了它。”他的声音很平静,没有一丝波澜,比窗外十二月的寒风还要冷。我低头,看见“离婚协议书”五个黑体字,像五个冰冷的烙印,烫在我的视网膜上。财产分割那栏写得很清楚,我们现在住的这......
第4章








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