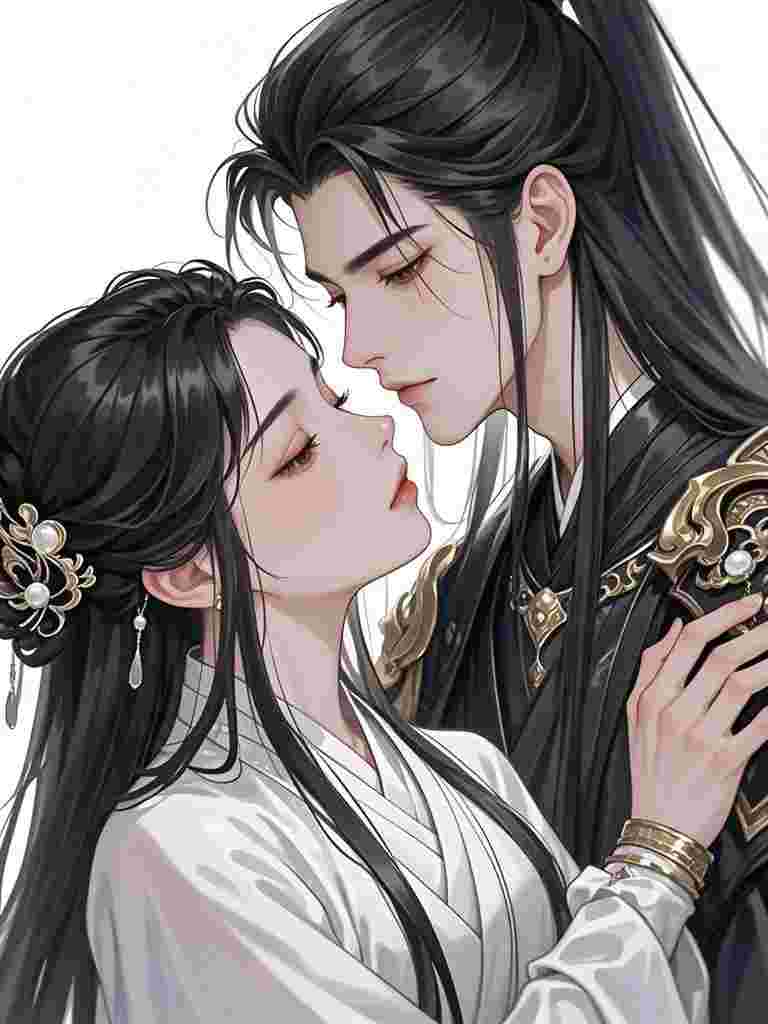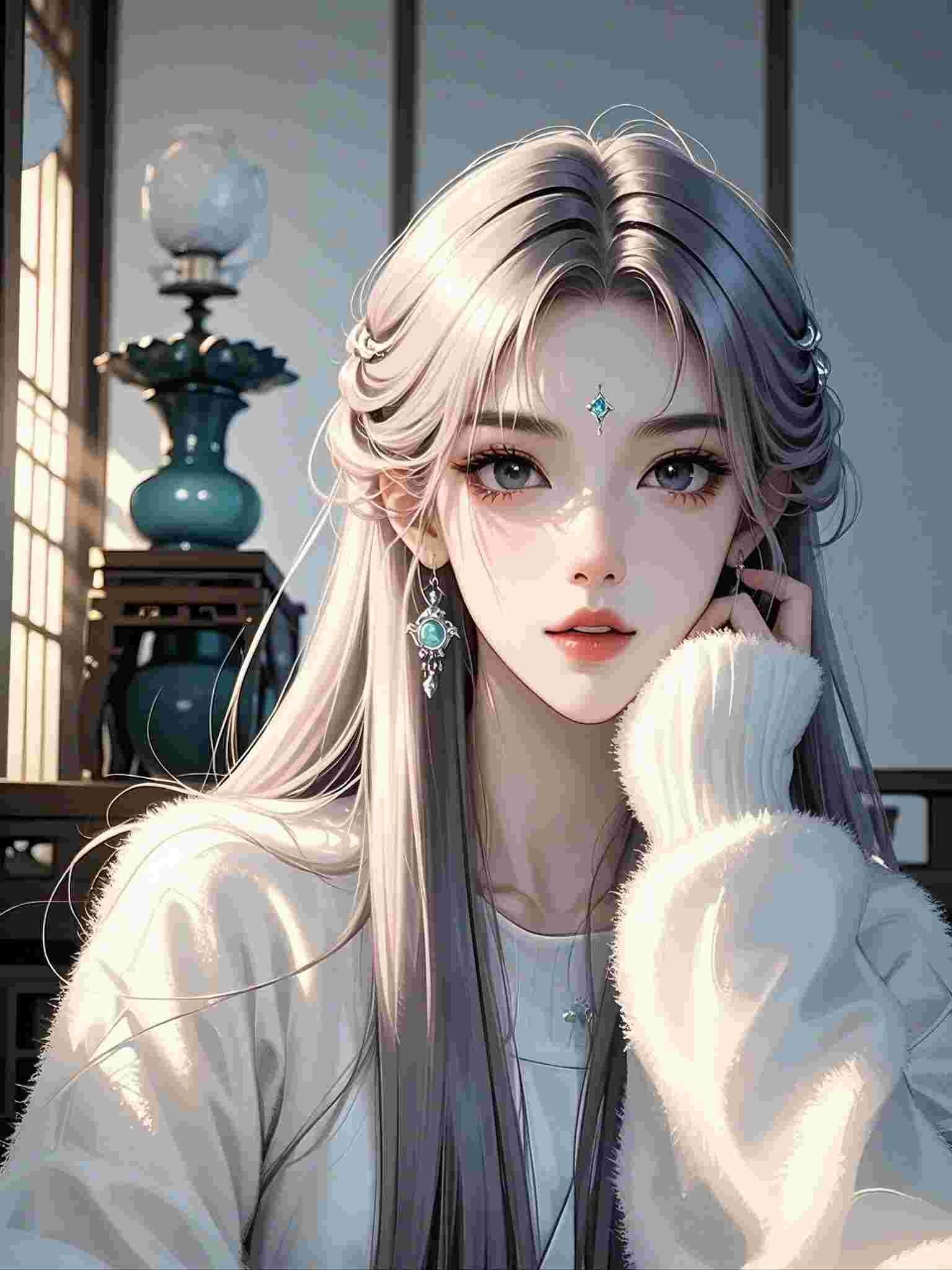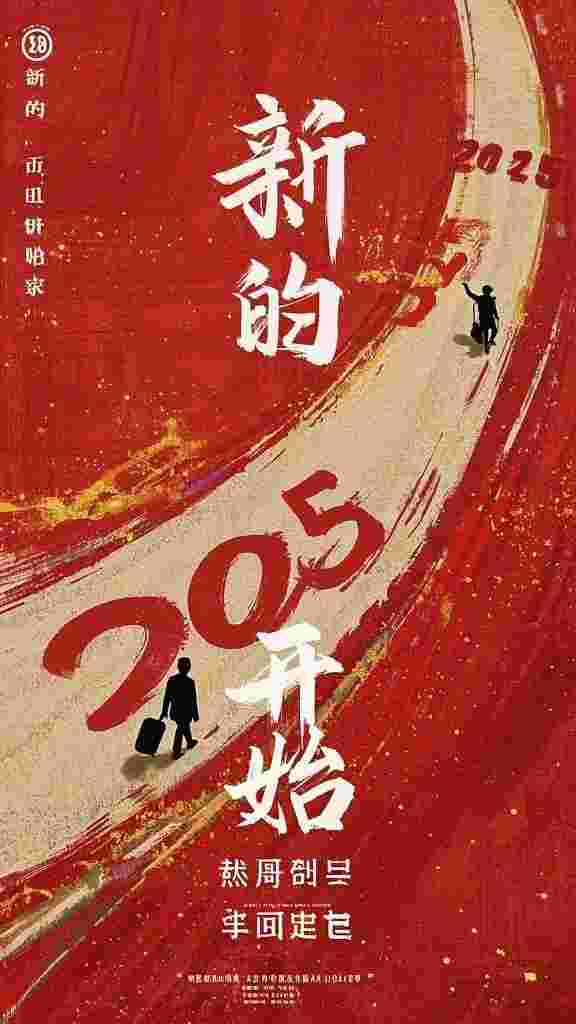越彻底。
“我为她花了多少钱!
你知道吗!
电影的投资!
我爸那边我费了多大劲才说通!
她呢?
连他妈一次正经的约会都不肯答应我!”
“还有上次那个姓张的导演,吃饭的时候眼睛就没从她身上挪开过!
要不是我拦着,手都要摸上去了!
我真想废了他!”
每一次,我都会扮演一个完美的倾听者。
我从不主动提建议,只是在他情绪最激动的时候,用一种看似无意的方式,抛出一些引导性的话语。
比如,当他抱怨孟棠不给他别墅的钥匙时,我会“不经意”地说:“唉,云顶别墅的安保系统是出了名的好,听说指纹和密码是双重验证,没有主人的允许,谁也进不去。
孟棠老师这么注重隐私,也是可以理解的。”
这句话,表面上是在为孟棠开脱,实际上,却是在他的潜意识里,植入了一个信息:别墅,有指纹和密码锁。
当他咒骂那些“情敌”时,我会在一片狼藉的酒瓶中,拿起一个,对着灯光“欣赏”:“高先生,您看这瓶威士忌,瓶身真漂亮。
要是……用这个砸在人头上,肯定很疼吧?
不过也就当时疼一下,警察来了,顶多算个故意伤人。”
然后我会摇摇头,自言自语般地补充:“不像我们写小说的,总想着怎么才能做得……神不知,鬼不觉。”
高翔的眼睛会猛地亮一下,然后追问我:“什么叫神不知,鬼不......鬼不觉?”
我就会神秘地一笑,把话题岔开。
我从不给他明确的答案,我只负责在他的心里,种下一颗又一颗黑色的种子。
我让他相信,我懂他,我是他唯一的同类。
同时,我也在悄悄地“借”走一些东西。
一次他喝醉了,我送他回家。
在他那辆骚包的保时捷副驾上,我“捡”到了一根他掉落的头发。
另一次,在他抱怨孟棠不回他信息时,我“安慰”地拍了拍他的肩膀,用指甲,轻轻刮下了一点他外套袖口上的纤维。
还有一次,我“不小心”打翻了他的酒杯,在用纸巾擦拭的时候,留下了一枚他清晰的指纹。
这些,都是我为他准备的,“通往地狱的门票”。
他对此,一无所知。
他只把我当成一个可以宣泄所有阴暗情绪,并且能给出“有趣”启发的树洞。
他以为自己是猎人。

都说那起悬案是完美犯罪,那是我做的程净孟棠:(番外)+(全文)
推荐指数:10分
以程净孟棠为主角的现代言情《都说那起悬案是完美犯罪,那是我做的程净孟棠:(番外)+(全文)》,是由网文大神“喜欢帝冠的吴长青”所著的,文章内容一波三折,十分虐心,小说无错版梗概:一个被誉为“完美犯罪”的悬案,唯一的真相,掌握在凶手——也就是我的手中。我将以第一人称,平静地复盘那场由“终极背叛”催生,用“艺术”和“理性”精心编织的复仇盛宴。第1章 我是唯一的目击者七年了。距离那场震惊全国的“云顶别墅坠亡案”,已经过去了两千五百多个日夜。警方档案室的卷宗上,它的标签已经从“重大......
第7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