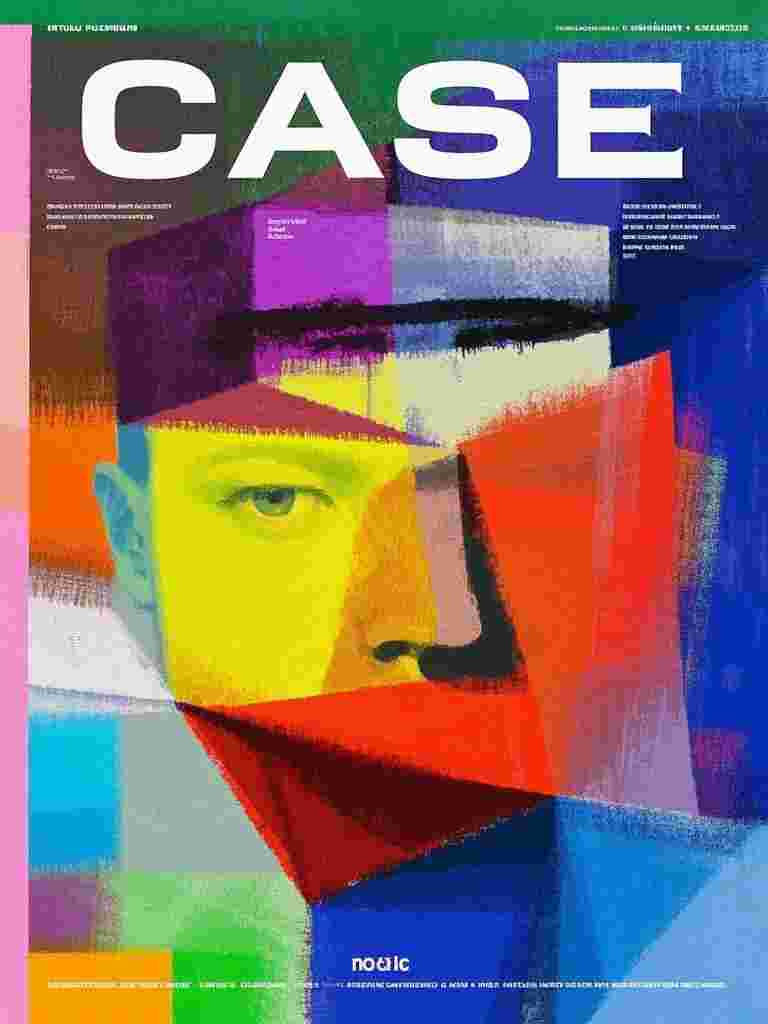却不敢多言。
老夫人。
那个躺在昏暗药气里、眼神却如老枭般锐利的老太太。
她看我时,说的那句“省得麻烦”……我心头一凛,面上却不动声色,只轻轻叹了口气,流露出几分哀戚:“姐姐去得突然,我连她最后一面都未见着。
若能得她一两件旧物,也是个慰藉。”
我拿起绢帕,按了按并无泪意的眼角,“罢了,许是母亲伤心,不愿再见旧物触景生情。”
春桃嘴唇动了动,似乎想说什么,最终却只是把头埋得更低。
我抿了口茶,水温正好,却暖不透心底的寒意。
看来,从明面上打听是行不通了。
这府里,处处是眼睛,处处是禁忌。
必须另想办法。
9接下来的两日,风平浪静。
陆云霄军务似乎极为繁忙,白日罕见人影,即便回来,也多在书房处理公务至深夜,偶尔来新房,不过是例行公事般的审视一圈,问几句不痛不痒的话,眼神依旧深沉难测。
我扮演着温顺安分的新夫人,每日晨昏定省去静心堂给老夫人请安。
老太太多数时候精神不济,说不上两句话便倦怠挥手让我退下,唯有那双眼睛,每次在我脸上逡巡时,都带着那股令人不适的审视与冰冷探究。
我小心翼翼地试探过两次库房的位置,皆被守在那里的老嬷嬷不软不硬地挡了回来,只说库房重地,闲人免进。
直到第三天夜里。
更深夜重,窗外起了风,刮得树枝簌簌作响,偶尔传来远处巡夜卫兵单调的脚步声。
身旁的陆云霄似乎睡熟了,呼吸平稳悠长。
我僵直地躺着,一动不动,直到确认她的呼吸节奏毫无变化,才极其缓慢地、一寸寸地挪动身体,掀开锦被,赤足踩在冰凉的地板上。
没有点灯,我借着窗外微弱的天光,像一抹游魂般悄无声息地滑出新房,掩上门。
廊下空无一人,只有檐角挂着的灯笼在风里摇晃,投下明明灭灭的光影。
我凭着白日观察的记忆,避开巡逻的岗哨,屏住呼吸,快速穿过一道道回廊,朝着后院库房的方向摸去。
库房所在的小院比静心堂更偏,院门落了锁。
我绕到院墙一侧,那里有一棵老槐树,枝桠恰好伸进院内。
心跳如擂鼓。
我提起旗袍下摆,咬着牙,借着树干粗糙的纹理,笨拙而艰难地攀爬。
指甲可能劈

出嫁后发现姐姐的日记本大帅陆云霄后续+全文
推荐指数:10分
以大帅陆云霄为主角的现代言情《出嫁后发现姐姐的日记本大帅陆云霄后续+全文》,是由网文大神“悦柒柒呀”所著的,文章内容一波三折,十分虐心,小说无错版梗概:大帅府的新房还贴着褪色的喜字。 姐夫陆大帅捏着我的下巴冷笑:“你姐姐死都不愿让我碰,你倒是识趣。” 我垂眸轻笑:“姐夫,我和姐姐不一样。” “她心里装着别人,而我——”我伸手勾住他的腰带,“只想做大帅夫人。” 深夜,我在姐姐的梳妆台暗格里找到一本日记。 翻开第一页,写着:“陆云霄是个女人。”1红烛滴......
第13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