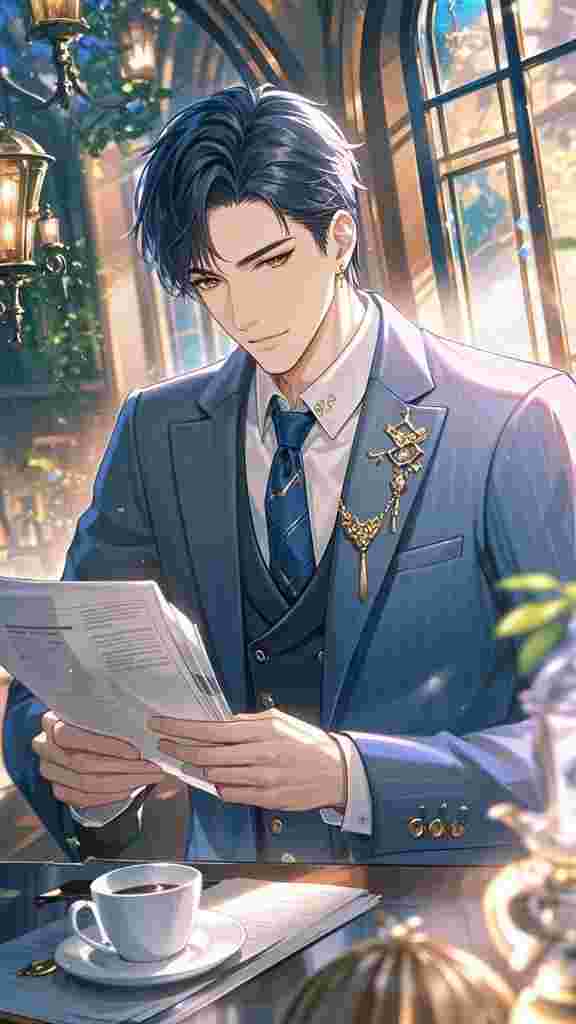火长明”这类字眼,笔锋算不上遒劲,却透着股踏踏实实过日子的稳当劲儿。
这天午后,阳光透过商行的木窗,在案几上投下细碎的光斑。
沈雁声刚写完一张“平安”,就见林墨棠抱着一叠新到的《良友》杂志走进来,脸上带着藏不住的笑:“你看!
咱们赞助的‘码头烟火摄影展’,照片登在杂志上了!”
她翻开杂志,指着其中一页:照片里,王老三正带着去年那个插队的年轻人卸货,两人扛着同一根扁担,脚步踩得又稳又齐,阳光把他们的影子叠在一起,像幅鲜活的画。
旁边配着林墨棠写的短文,字里行间全是对雾城的眷恋:“这里的江风带辣,江水带暖,每个人都在码头的号子里,把日子过出了热乎气。”
沈雁声看着照片,指尖轻轻划过纸面,突然想起第一次见那年轻人时,对方攥着扁担、急得眼圈发红的模样。
如今这后生不仅在码头站稳了脚,还跟着王老三学认字,偶尔来商行串门,会怯生生地请教他写字,日子肉眼可见地亮堂起来。
“对了,雷队长呢?”
林墨棠合上杂志,往后院瞥了一眼,没见着雷震川的身影。
“在后院教孩子们扎风筝。”
沈雁声笑着指了指窗外,“说要赶在清明前,让孩子们放着风筝去江边踏青。”
话音刚落,后院就传来孩子们的欢笑声,夹杂着雷震川的大嗓门:“慢点扯线!
风筝要顺着风走,跟做人一个道理,得懂变通!”
两人走到后院,就见雷震川蹲在地上,手里拿着竹篾和彩纸,正教几个半大孩子扎风筝骨架,地上已经摆着两个做好的,一个画着嘉陵江的江猪子,一个画着码头的幡旗,颜色鲜亮得很。
“沈先生,林姐姐!”
孩子们见他们来,立刻围过来,举着手里的彩纸,“帮我们画个茶馆的灯笼吧!”
林墨棠笑着接过彩笔,沈雁声也蹲下身,帮孩子们固定竹篾。
阳光洒在院子里,混着孩子们的笑声,还有远处码头传来的号子声,暖得人心头发胀。
傍晚时分,雷震川带着孩子们去江边试放风筝,林墨棠举着相机跟在后面,沈雁声则留在商行整理账本。
刚把账目理完,就见杜老七拎着个竹篮走进来,篮子里是刚蒸好的红糖发糕,还冒着热气:“歇会儿

天机·雾城暗棋『下』无删减+无广告
推荐指数:10分
《天机·雾城暗棋『下』无删减+无广告》是作者 “逸墨素笺”的倾心著作,沈雁声江雾是小说中的主角,内容概括:导语:鱼嘴码头的枪声散去,张胖子的阴谋终露原形,沈雁声父亲的冤屈随江水淌过,化作老鹰茶咽下去的回甘。当“雾江商行”的红灯笼照亮码头石阶,当“江神祭”的长桌宴摆满街坊的拿手菜,当年那盘剑拔弩张的“暗棋”,早已在挑夫的号子、孩子的笑声与火锅的红油里,落子成寻常日子的暖。这后半程的故事,没有惊心动魄的对峙......
第6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