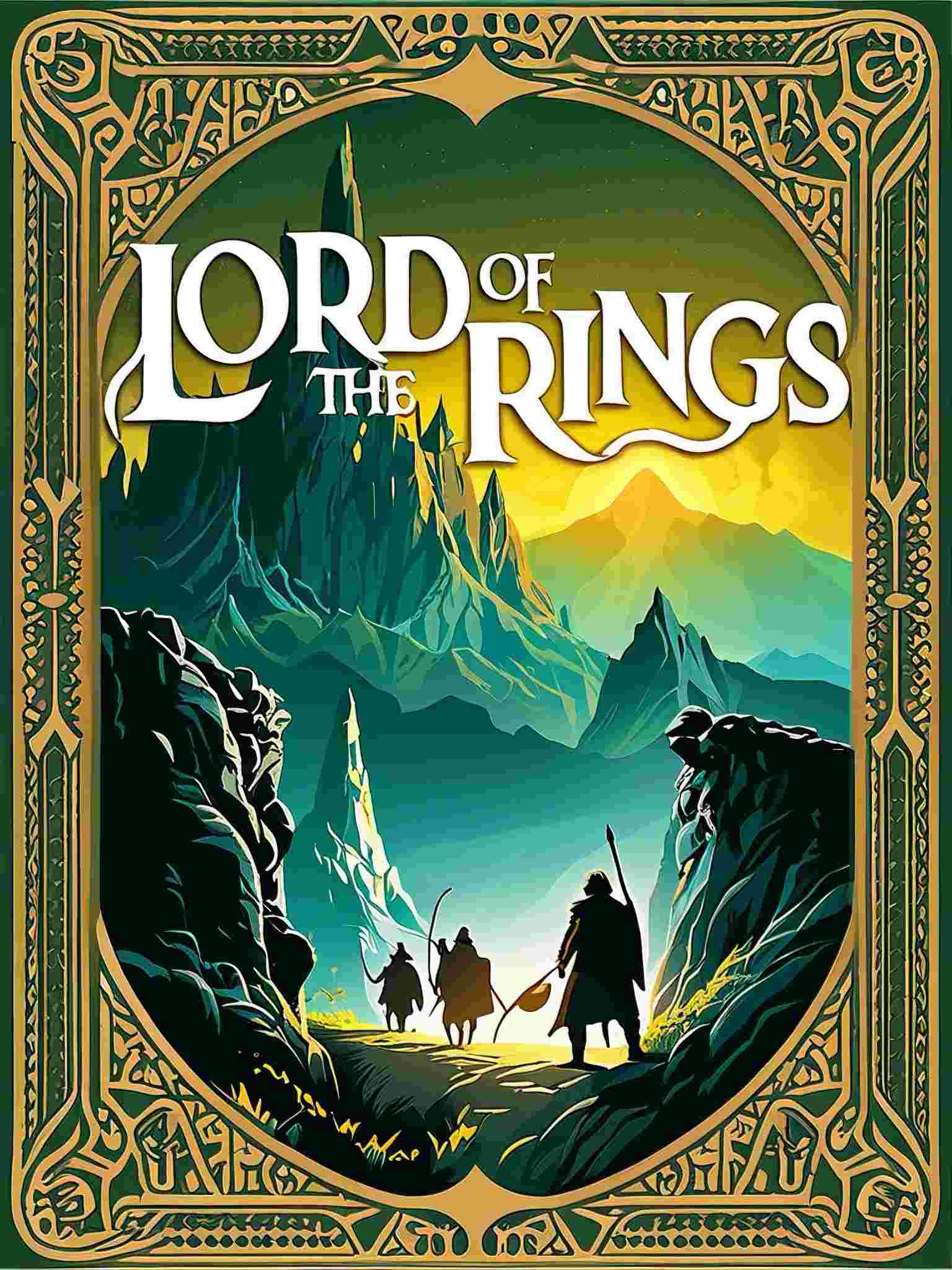没有恨,只有一片死寂的灰。
后来我才知道,他那天在雨里跪了三个时辰,直到衙役来拖他走。
走前,他摸了摸无名指上的铜戒——那是我十五岁随手赏他的,值不了几个钱,他却当宝贝似的戴着。
北境的风雪,比姜府的雨狠一万倍。
充军路上,他脚镣磨穿脚踝,血在雪地拖出断续红线,像一条蜿蜒的毒蛇。
押解官克扣口粮,鞭子抽在他背上,皮开肉绽,他一声不吭,只把《充军令》捂在胸口——仿佛那薄薄一张纸,能暖他将死的身。
行至风雪垭口,运粮官嫌他拖慢进度,一脚踹他跪在冰河上。
冰面如镜,映出他惨白的脸,和身后连绵的、望不到头的雪山。
“磨蹭什么?
等狼来叼你?”
运粮官啐了一口,马鞭抽在他背上。
他跪在冰面上,嘴唇冻得发紫,却忽然笑了,从怀里掏出那张被雪水泡烂的《充军令》,对着垭口方向——那是姜府的方向,轻轻说了句:“…小姐保重。”
那是他最后一句话。
当夜,暴风雪吞没垭口。
他蜷在冰窟窿里,体温降至冰点,幻觉中看见我撑伞走来,伞下还带着姜府后院的梅香,我穿着那件他最喜欢的月白襦裙,对他笑。
——实际,我正在暖阁,亲手给三叔姜承业包扎被账册划伤的手。
“侄女,”三叔拍我肩,热茶的雾气熏红了他的眼,“多亏你果断,不然咱家全完了。”
我低头应是,指甲掐进掌心,掐出了血。
七日后,管家送来一个木匣,匣上沾着北境的雪泥。
匣中是一张照片——野狗叼着他右手,无名指上还套着我赏的铜戒,戒圈被狗牙咬得变形,却仍固执地套在指骨上。
照片背面,他用最后的血,歪歪扭扭写了三个字:“…保重。”
我盯着照片,铜戒在野狗齿间泛着冷光——那戒指内圈,刻着一个小小的“漪”字,是我无聊时拿簪子刻的,他竟一直戴着。
“小姐,”管家声音发颤,“仵作说…他死前,把《充军令》塞进嘴里,嚼烂了咽下去——怕被野狗叼走,污了您的名。”
我猛地将照片扣在案上,茶盏打翻,茶水洇湿“保重”二字,像血泪。
“烧了。”
我声音发颤,喉咙像被砂纸磨过,“连灰…都别留。”
那晚,我烧了所有他经手的账册,火盆里的

三世赘婿之温砚之的死亡报告全章+后续
推荐指数:10分
经典力作《三世赘婿之温砚之的死亡报告全章+后续》,目前爆火中!主要人物有姜承业姜明漪,由作者“醉月葵”独家倾力创作,故事简介如下:红烛烧到一半,蜡泪堆叠如血痂。姜府东苑,满堂“百年好合”的喧嚣早已散尽,只剩我和他——一个刚被家族塞来的赘婿,一个被迫成婚的贵女。温砚之坐在三步之外,喜服如新,笑容温润,像一尊精心雕琢的玉像。可我知道,玉像底下,藏着刀。上月库房失窃的南海珠,至今未破。而眼前这个男人,恰在案发三日后,被父亲“慧眼”选......
第4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