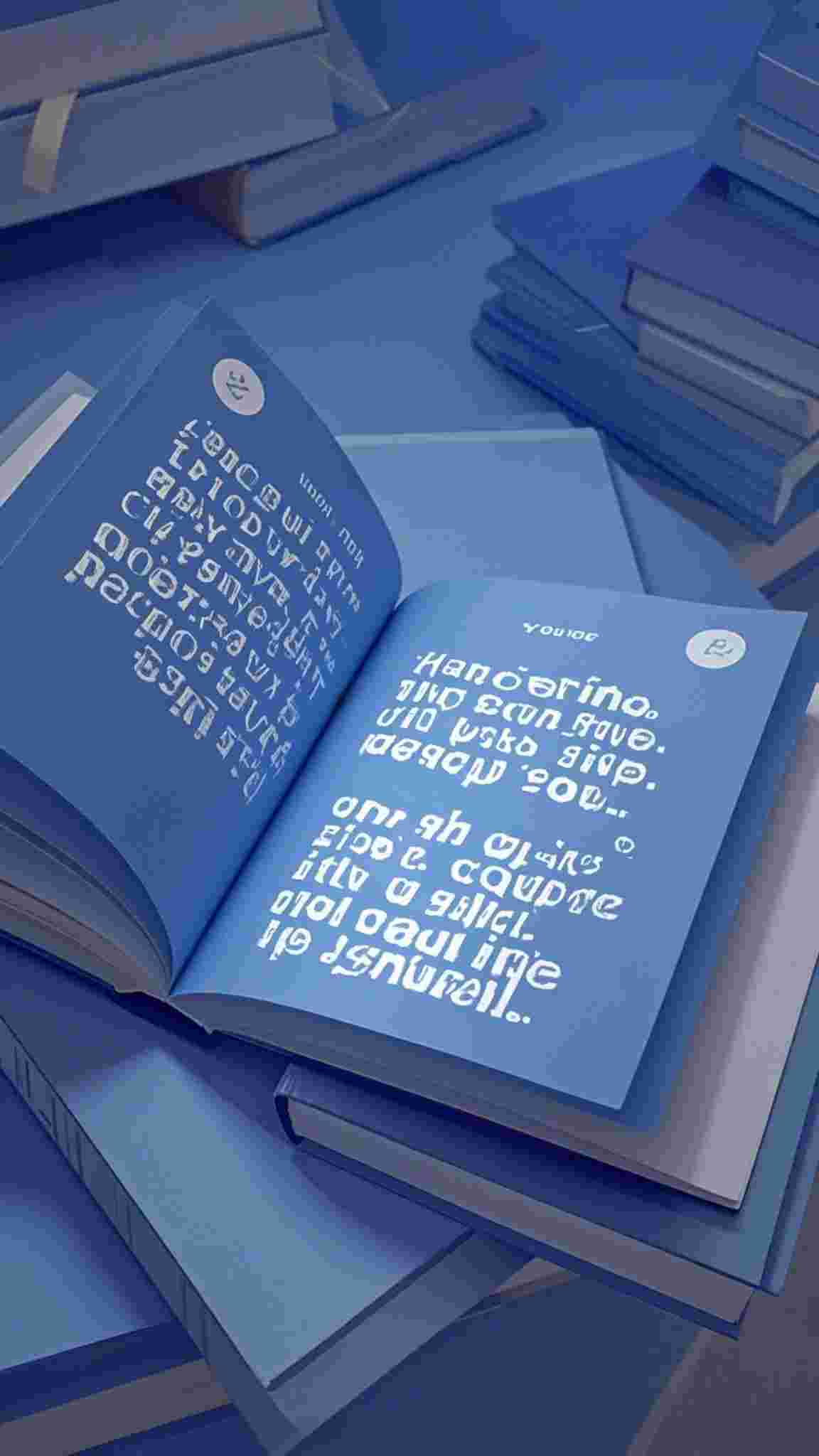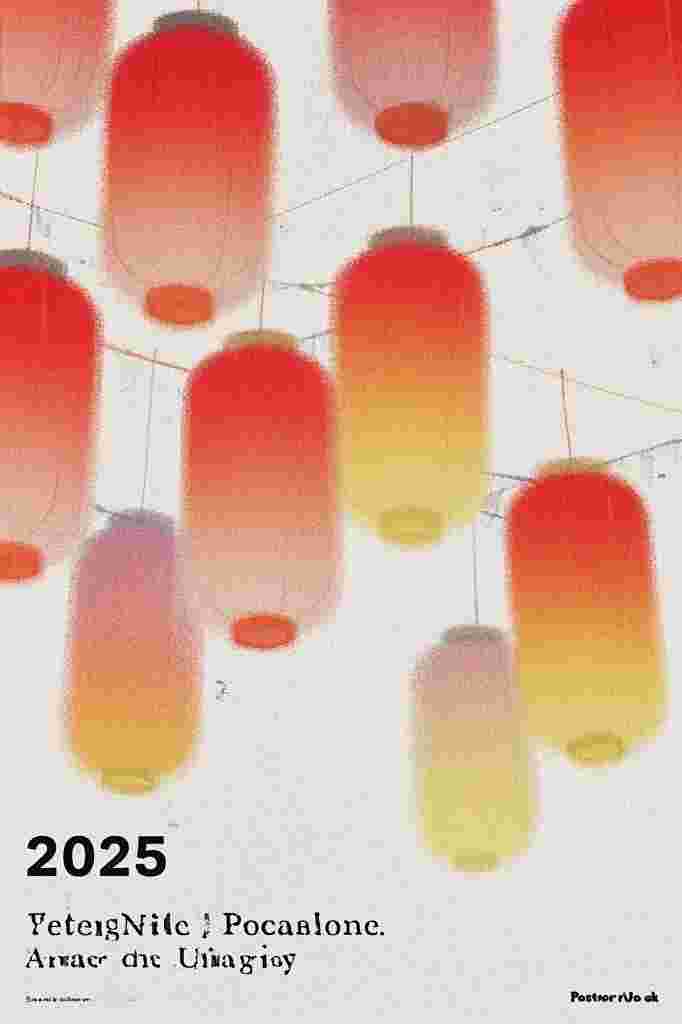。”
我表示疑问,但还是友好表示,“禾潇同学,你好。”
祝涔也人机般跟着我说,“你好。”
她微微一笑,“我是林浔的同班同学,之前总是看到你们三个一起。”
“我懂你们的世界或许失衡,你们需要时间来慢慢重构,又或是沉溺其中。”
“但我已经很久没有在墙上看到你们了。”
这是林浔去世后,第一次被他人提起。
禾潇说的墙是指教学楼大厅一面写满排名的墙。
每次月考后,学校根据试卷难度,预测重点一本分数线,分数线以上的人,会上墙。
反之,下墙。
“林浔在班上会提起你们。”
说完,她潇洒离开。
我明白她的意思。
林浔会惦记我们。
我们会一直记着林浔。
死亡不是终点。
我的生命要有意义,我的思念才更有份量。
我无比感谢她,一个对我们伸出援手的女生。
我无比感谢她,坦然地谈到林浔。
这何尝不是林浔送给我们的礼物。
一直到清明节。
今年,我终于明白了。
什么叫“一山有一山要见的人”。
我和祝涔在林浔坟前絮絮叨叨的。
说我们两个的颓废,说我们两个吃不好睡不好。
说学校对面开了新店,说大学霸禾潇。
说风融了风,云卷云舒。
清明小雨打在我们身上,淋湿了我们三个。
如此,我们或许可以卸下一丝沉重。
相机咔嚓,留下一张合照。
晚自习,返校时,父母才告知我云姨又怀孕了。
冒着高龄孕妇的风险。
我仍记得她说女生就是要读书,我仍记得她说尽女性的悲哀,我仍记得她对我的好。
我与祝涔沉默不语。
我在心里想,今年,云姨又在坟前磕头了吗?
说忏悔,求保佑。
又在保佑是个男孩吗?
这次,会叫什么名字呢?
从那以后,我和祝涔发奋图强,立志要上墙。
时间一晃而过,高二下学期,我们终于实现了这个目标。
这期间,我们带着我们的进步奖状和礼物,去给林浔过了他的十七岁生日。
还有他一岁的时候。
我们留下了许多合照。
临近过年,云姨冒着生命危险,生下了一个男孩,取名为林安。
意为平平安安。
祝涔也被允许回去了。
大年初一阳光正好,我和祝涔又回到云姨的小院。
邻居们围着小孩,七七八八地说着。
云姨的笑声从耳边传来。
堂屋里,林焰哥的灵

车祸拿我朋友开刷(十年一死两伤祝涔林浔全文+后续+结局
推荐指数:10分
以祝涔林浔为主角的现代言情《车祸拿我朋友开刷(十年一死两伤祝涔林浔全文+后续+结局》,是由网文大神“拘云是什么云”所著的,文章内容一波三折,十分虐心,小说无错版梗概:十六岁那年,我接到电话,我的好朋友出车祸死了。二十六岁那年,我接到电话,我的好朋友出车祸,昏迷不醒。十六岁前,我们三个是最要好的朋友。十六岁后,我们的合照变成了,我,祝涔和一个小土堆。我的好朋友死了,他叫林浔。大人们都说那是水中寻找的意思。可他告诉我,那是沉稳,顺遂,自由。他死在了意气风发的16岁。......
第8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