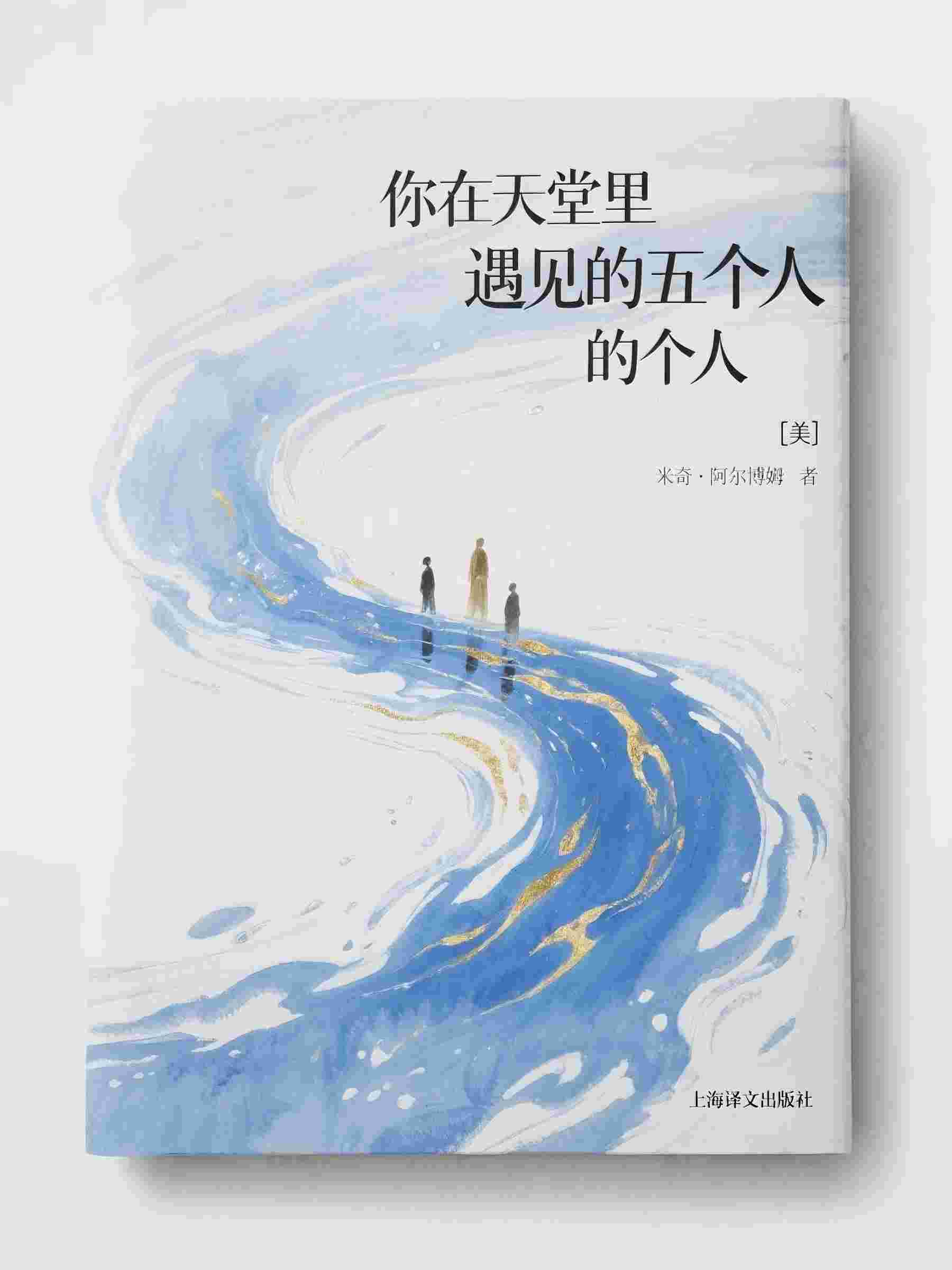村的人很快嚼上闲话:封二家新来的女人是朵带刺儿的野山茶。
大清早锦绣拎着木桶去井沿打水,汉子们的眼珠子粘在她鼓胀的胸前和微翘的臀线上。
“跟着唱戏的跑出来,一看就是个不安分的!”
豆腐坊的王掌柜腆着脸趁她提水时捏她一把,“封二那老杆子,骨头都能敲鼓了,还能管得了你这浪蹄子?”
锦绣手腕一抖,沉重的辘轳把哐当砸在王掌柜穿着破棉鞋的脚趾上,杀猪般的嚎叫声里,她勾起嘴角笑了笑,眼神却跟冰凌子似的。
那天傍晚封二借着半斤地瓜烧的劲儿,给了她一巴掌,唾沫星子喷了她一脸:“贱货!
全村老爷们的裤裆你是不是钻遍了?!”
锦绣舔了舔磕破的嘴角渗出的腥甜,突然像被踩了尾巴的野猫一样扑上去,一口咬在他布满褶子的颈侧:“是钻了!
个个比你强百倍!”
日子就在这种鸡飞狗跳、冷嘲热讽里过去,她竟然怀上了。
封二醉醺醺摸着她的肚皮,难得有丝热气:“你得给我生个小子…老天爷保佑,让我封二有后…”胎儿五个月大时,有天半夜锦绣肚子有点难受,忍不住哼唧两声。
封二被吵醒,恼了,一脚把她从热炕上踹下来:“嚎丧呢?
再哭咧咧老子给你扔出去!”
不知道从哪个嚼舌根的那儿听说云生曾经是她相好的,一股邪火拱上来,揪着她头发往墙上撞:“你那唱戏的小白脸儿回来啦!
在镇上搭台子呢!
滚去找你那情郎啊!”
锦绣护着肚子缩在冰冷的灶坑根下,一股热流顺着腿根往下淌,她抬头看着暴跳如雷的封二,反倒咧开嘴笑了,笑得比哭还难看。
村里的赤脚医生摇摇头:“是个成形的男胎…可惜了。”
封二血红着眼睛,摔了家里最后一个豁口陶碗。
第二年冬天,腊月里祭灶那天,封二喝得烂醉,回来的路上栽进了村边清水河上那眼不知被谁凿开捞鱼的窟窿里。
他头朝下,大半截身子卡进冰窟窿。
等捞上来,人胀得像鼓,青紫发亮。
锦绣木着脸盯着那张泡得变形的脸,一滴泪也挤不出来。
出丧那日,纸钱漫天飘飞。
人群里,不知谁啐了一口:“克死男人的丧门星!”
几个老婆子赶紧扯自家闺女往后躲。
锦绣听见了,没抬眼,嘴角却古怪地向上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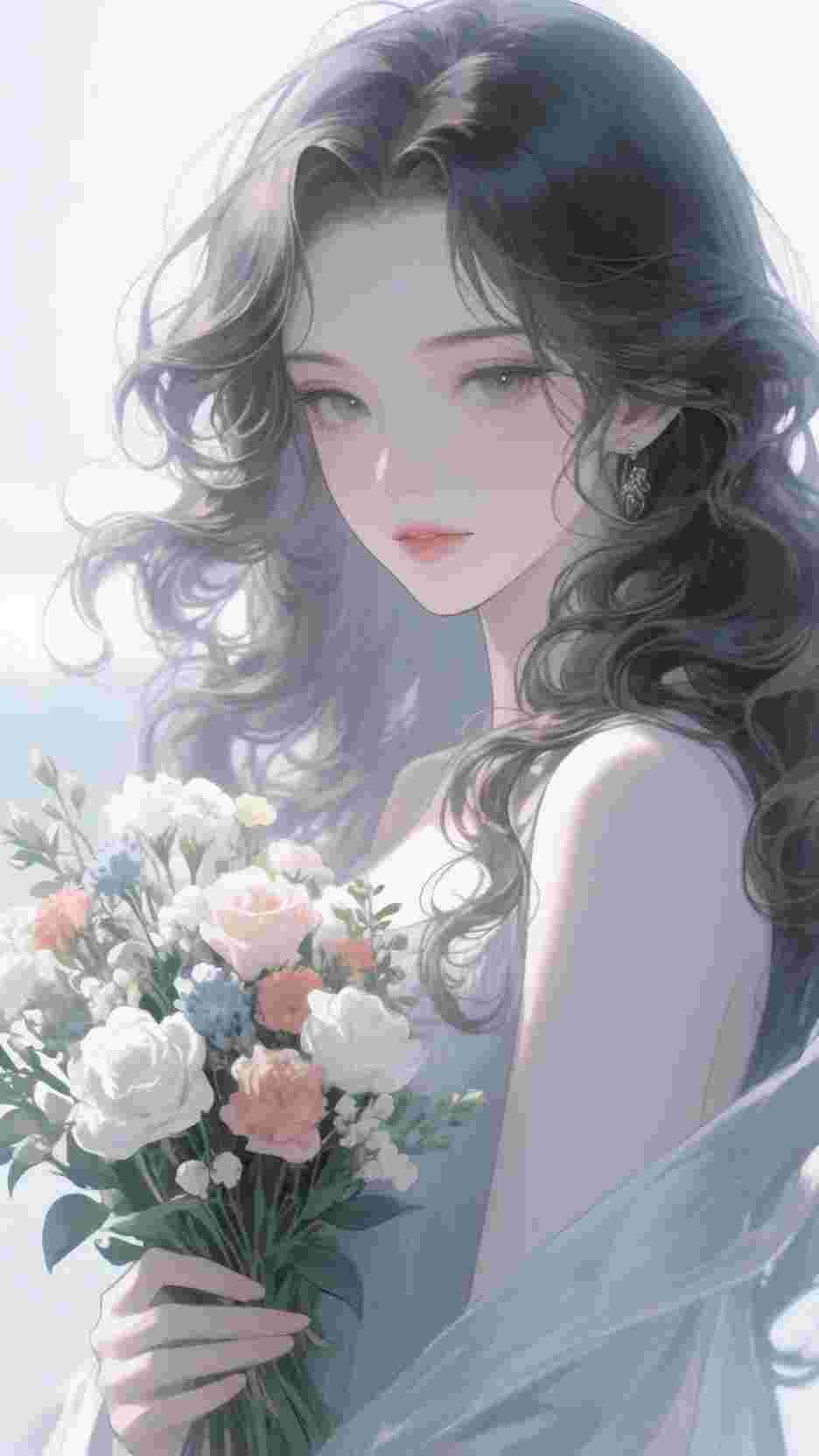
她奔光而去,却焚尽自己招娣王招娣无删减+无广告
推荐指数:10分
现代言情《她奔光而去,却焚尽自己招娣王招娣无删减+无广告》,是作者“申若鱼”独家出品的,主要人物有招娣王招娣,故事节奏紧凑非常耐读,小说简介如下:大雪封山的腊月里,七十多岁的锦绣蜷在土炕上,窗外的北风抽打着破败的窗棂,发出声声凄厉的呜咽。炭盆里最后一点火星熄灭了,她干枯的手指无意识地在粗布被面上划着,仿佛在计算着这漫长又短暂的一生。十四岁那年,也是这样的风雪天,锦绣彼时还叫王招娣,抱着父亲的灵位跪在村口。火光映着母亲灰败的脸:“妮儿,往后就剩......
第4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