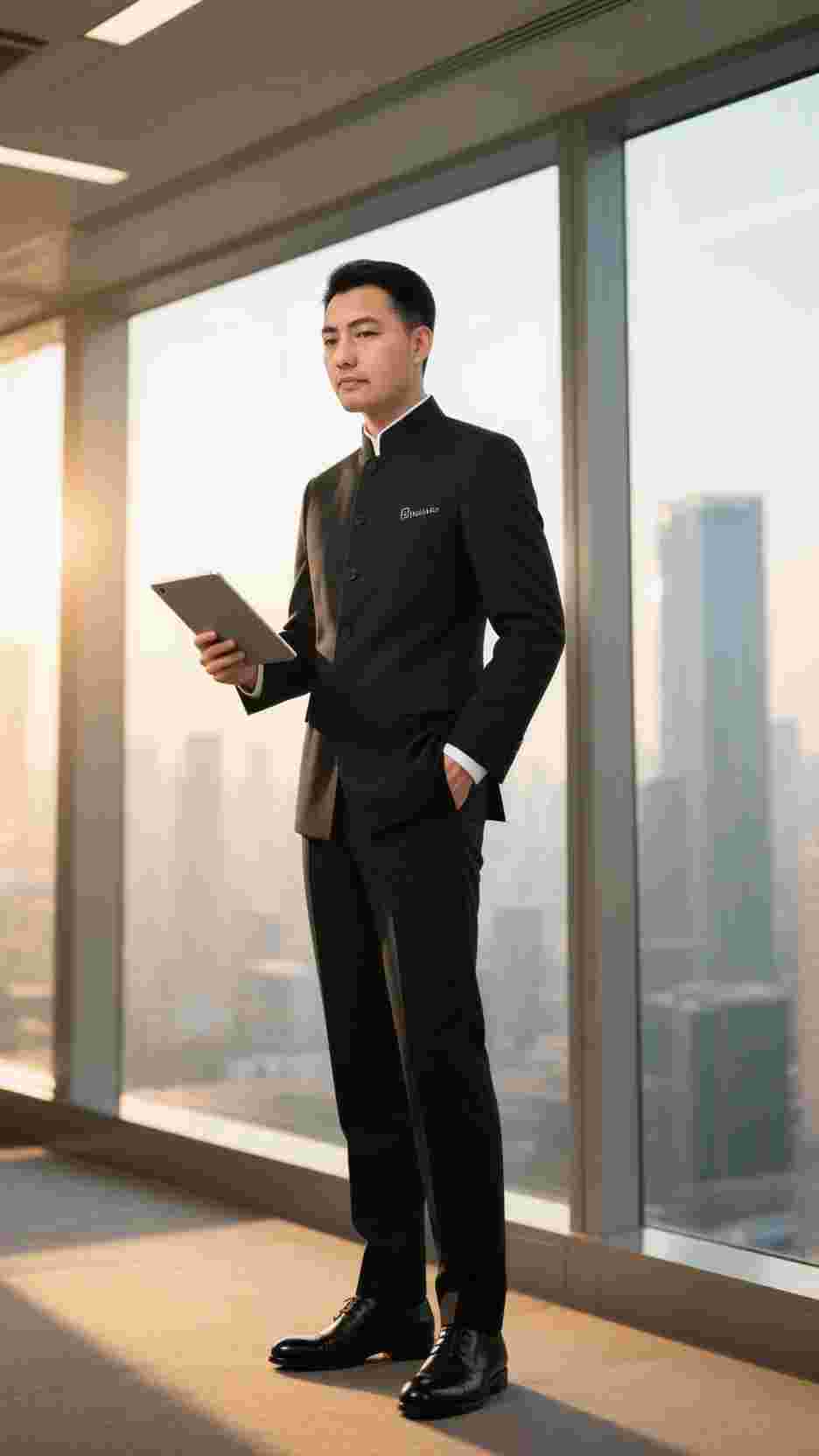,眼神里翻涌着剧烈的痛楚和一种被背叛的愤怒,声音嘶哑得像是砂纸在摩擦:“陈默!
你太让我失望了!
太让组织失望了!”
失望。
这两个字像淬毒的针,狠狠扎进心脏最深处。
然而,就在这巨大的屈辱和剥离感几乎要将我吞噬的瞬间,一种奇异的、冰冷的清醒感,如同深海的暗流,从意识的最底层悄然涌起。
所有的喧嚣、所有的指控、所有的目光,仿佛都在离我远去。
胸腔里那片空荡荡的位置,仿佛还残留着警徽冰冷的金属触感。
那不仅仅是警徽的重量,更是……某个微小而精密的装置启动的信号。
一丝极其微弱的、几乎无法察觉的电流感,似乎从那个空荡荡的位置传来,像幻觉,又像某种冰冷的确认。
在赵铁山痛心疾首的怒吼声里,在督察队员冰冷的手即将搭上我肩膀的那一刻,在所有或震惊、或鄙夷、或痛惜的目光聚焦下——我缓缓地、缓缓地抬起了头。
脸上没有任何表情,没有愤怒,没有辩解,没有委屈。
只有一片近乎冷酷的平静。
然后,我的嘴角,极其缓慢地,向上扯动了一下。
一个无声的、冰冷的、带着一丝疯狂意味的弧度,在唇角悄然绽放。
我笑了。
冰冷的金属门在身后沉重地合拢,发出沉闷的“哐当”声,隔绝了走廊里最后一点光线和声响。
禁闭室狭小、逼仄,四壁是冰冷的、吸音的灰色软包材料,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消毒水和陈腐灰尘混合的味道,沉闷得令人窒息。
唯一的光源是头顶一盏低瓦数的白炽灯,光线昏黄,投射下浓重的阴影,让房间显得更加压抑。
督察队员离开的脚步声彻底消失,整个世界只剩下自己粗重的呼吸声,还有血液冲击太阳穴的沉闷鼓点。
我背靠着冰冷的门板,缓缓滑坐到同样冰冷的地板上,身体里的力气仿佛被瞬间抽空。
胸前的警徽被摘走的地方,留下一种尖锐的空洞感,一种被强行剥离的耻辱,冰冷地烙印在皮肤上,直刺心底。
赵铁山那句“你太让我失望了!”
还在耳边嗡嗡作响,像毒蛇的信子舔舐着神经。
实验室里那些震惊、审视、甚至带着恐惧的目光,如同幻灯片一样在眼前反复闪现。
失望?
信任?
我猛地攥紧拳头,指甲深深掐进掌

证物抖音热门全文
推荐指数:10分
小说《证物抖音热门全文》新书正在积极地更新中,作者为“淡淡的小脑斧”,主要人物有抖音热门,本文精彩内容主要讲述了:挡风玻璃上,世界被彻底揉碎。雨刮器疯了似的左右摇摆,刮开两道混沌的扇面,只一瞬,又被狂暴的雨水重新糊成一片灰蒙蒙的泥汤。车灯的光柱刺出去,像两把钝刀在墨黑的雨幕里徒劳地劈砍,勉强照亮前方几米湿滑扭曲的路面。引擎盖在密集的雨点敲打下,发出沉闷而持续的鼓点。车里闷得像蒸笼,空气里弥漫着湿衣服捂馊的气味、......
第9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