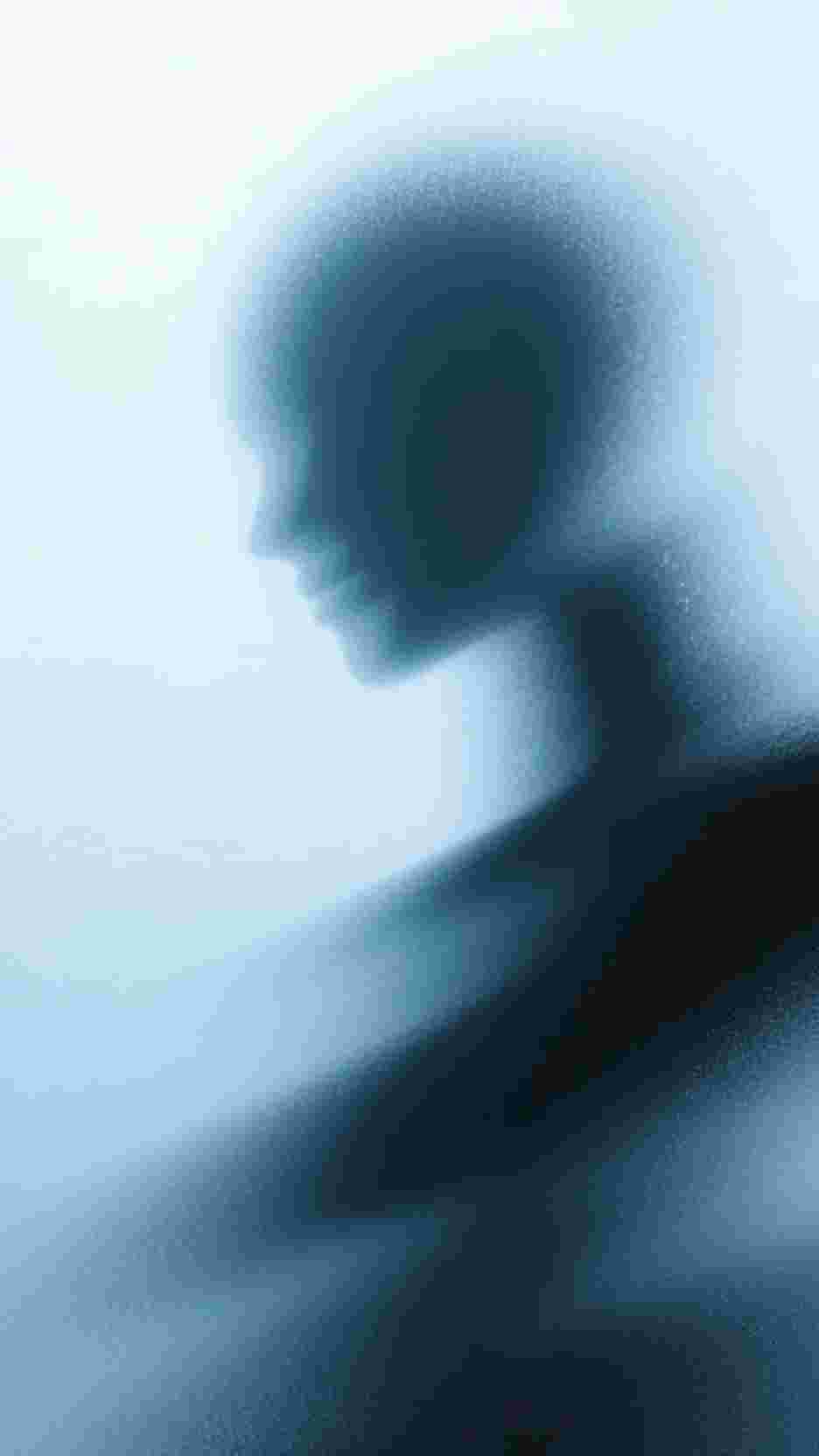照顾他、生儿育女,我也就认了。”
水晶灯的光落在她发烫的耳尖,林晚秋放下刀叉:“阿姨,我读大学不是为了当家庭主妇的。”
那晚她在华大湖畔坐了很久,赵母的话像根刺扎在心里。
如果答应,弟弟的彩礼、家里的新房都能解决,她再也不用为学费发愁。
可一想到灶膛边的晨光、秦岭孩子的眼睛,心口就像被撕开道口子。
江译找到她时,手里拿着本《我是青年》的单行本:“我就知道你会在这里。”
他在她身边坐下,没追问什么,只是轻声念起诗来。
月光洒在两人交叠的影子上,她忽然靠在他肩头,眼泪打湿了他的衬衫。
暑假的秦岭之行,江译申请作为志愿者同行。
当她在塌方路段背着课本深一脚浅一脚地挪时,他始终走在前面开路,不时回头伸手拉她一把。
那个叫央金的藏族女孩,总在她备课的篝火旁唱着古老的歌谣,眼睛却偷偷瞟着帮她们修黑板的江译。
离开那天,央金把亲手绣的向日葵挂在她包上:“老师说,你就像这花。”
而江译被孩子们围着要签名时,悄悄把枚向日葵形状的书签塞进林晚秋手里。
大四那年,林晚秋同时收到了保研通知和公益基金会的录用函。
赵宇恒最后一次找到她时,手里捏着钻戒盒:“我妈说了,你要是改变主意,婚礼日期都订好了。”
林晚秋指着公告栏里自己的名字 —— 她的论文获得了国家级优秀奖项。
“这才是我想要的。”
她的声音很轻,却带着前所未有的坚定。
江译在公告栏另一侧贴完自己的获奖证书,转头对她笑了笑,眼里的光和初见时一样明亮。
毕业典礼上,她作为优秀毕业生发言,江译在台下举着那本《郭小川诗选》,扉页上的向日葵图案已经褪色。
“我曾站在十字路口犹豫,” 她望着台下的周月和语文老师,也望着江译,声音里带着哽咽,“但有人让我记得,青年应当像河流一样,朝着开阔处奔涌。”
阳光穿过云层落在她身上,恍惚间又回到那个河边的午后,白衬衫的女生读着诗,河水闪着碎金般的光。
去基金会报到前,她回了趟老家。
老医生的药箱还摆在堂屋,只是多了台电脑,屏幕上正播放她录制的网课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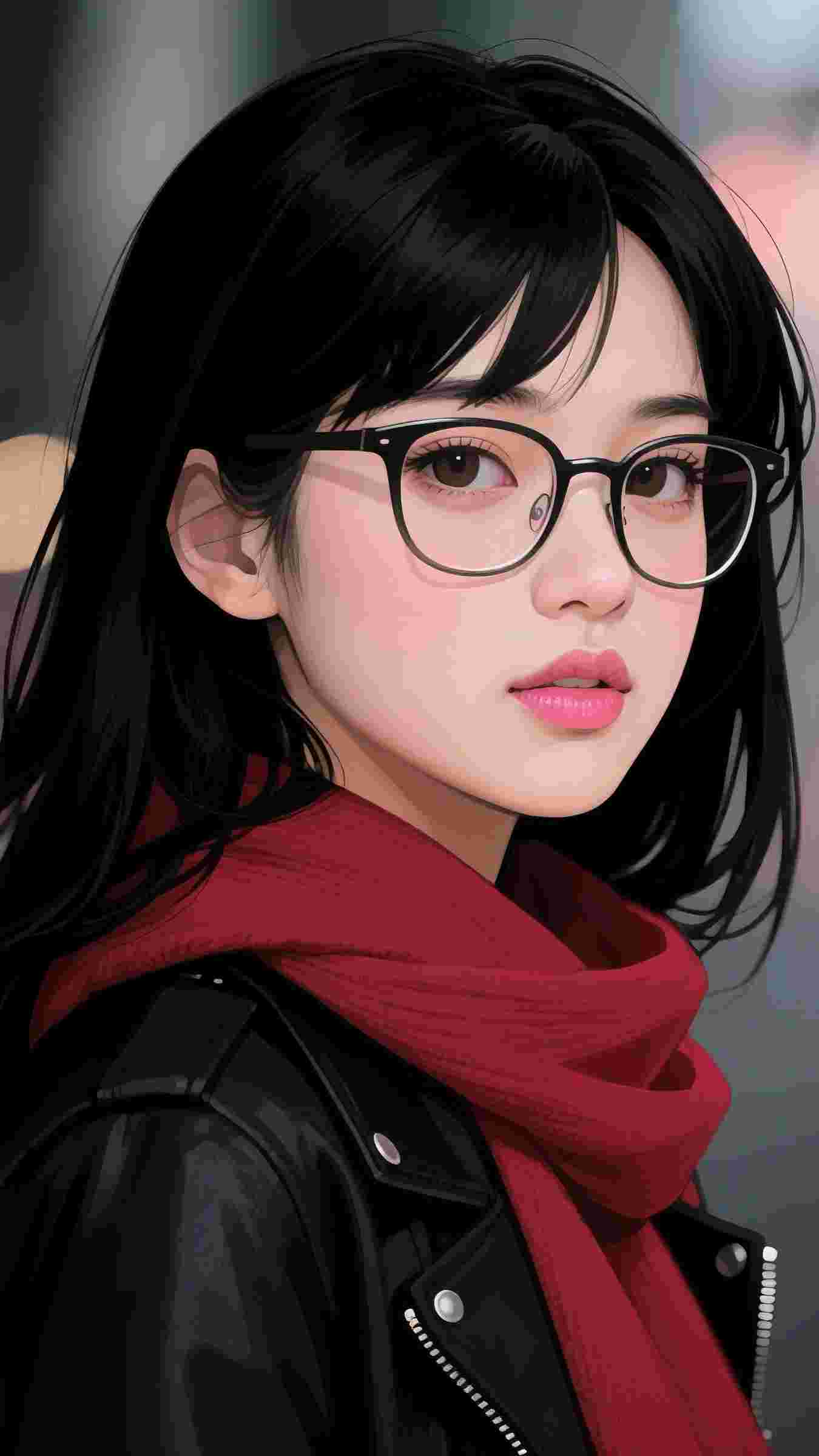
要发光,而非被照亮结局+后续
推荐指数:10分
《要发光,而非被照亮结局+后续》是由作者“yqdp”创作的火热小说。讲述了:灶膛里的火光舔着锅底,把林晚秋的影子投在土墙上映得忽明忽暗。她攥着皱巴巴的五毛纸币,指甲深深嵌进掌心 —— 这是她攒了半个月的早餐钱,再凑三张就能买到那本封面磨出白边的《现代汉语词典》了。“晚秋,把你那点钱给妈。” 母亲掀开门帘进来,围裙上还沾着灶台的烟灰,“你弟要买游戏机,同学都有。”“可是……”......
第7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