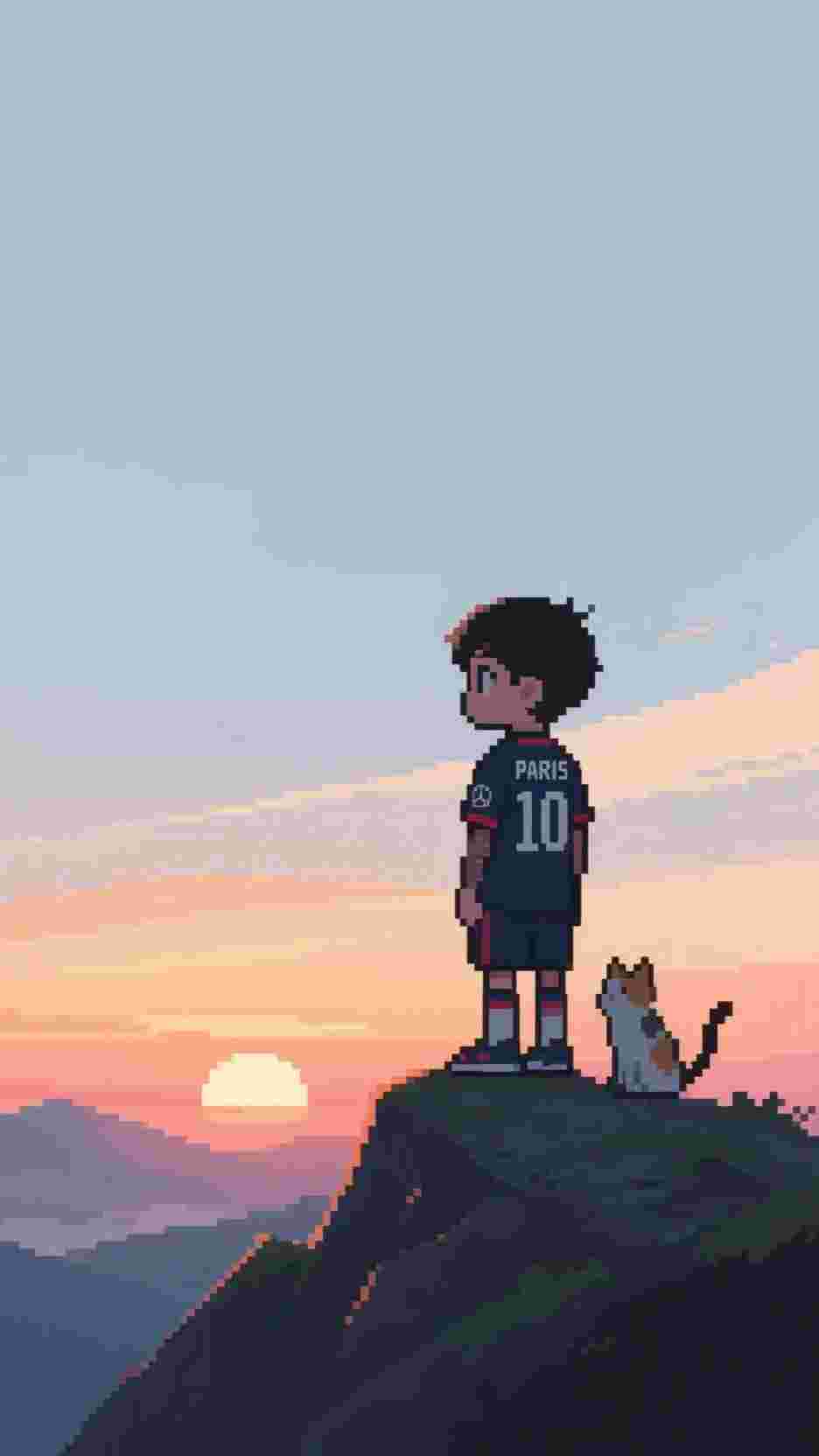来。
死寂。
比坟墓更深沉的死寂。
连磷火都仿佛凝固了。
只有风卷着纸灰,发出呜咽的悲鸣,还有那粘稠黑血从巨大伤口涌出的、令人毛骨悚然的“汩汩”声,像地狱的计时沙漏。
马背上那个为首的高大身影,如同一个设定好程序的冰冷傀儡,缓缓地、毫无生气地转动了头颅。
那双隐藏在浓重阴影深处的眼睛(如果那阴影里真的有眼睛的话),如同两口通往九幽寒狱的冰井,精准地、毫无感情地锁定了我。
那目光,没有愤怒,没有好奇,只有一种看待物品的、彻底的漠然。
那目光扫过我沾满污泥和血污、因极度恐惧而扭曲痉挛的脸,扫过我因剧烈喘息而起伏的胸口,最终,如同两枚淬了剧毒的冰针,死死钉在了我颈间那个随着我身体无法抑制的剧烈颤抖而晃动的、绣着“奠”字和诡异鸳鸯的暗红荷包上。
他开口了。
声音不高,低沉沙哑,却像冰冷的砂轮在锈蚀千年的铁棺上缓缓摩擦,每一个字都带着沉重的死亡气息和一种非人的、空洞的回响,清晰地碾过我的耳膜,砸进我的意识:“‘阴缘’……已成?”
语调毫无起伏,冰冷得不带一丝疑问,更像是在宣读一份早已盖棺定论的死亡判决书。
那声音,那冰冷的、如同锈铁摩擦的宣判,像一根烧红的冰锥狠狠扎进我的天灵盖,瞬间冻结了思维。
颈间的“奠”字荷包,仿佛瞬间活了过来,变成了一条冰冷滑腻的毒蛇,死死缠紧我的喉咙,勒得我无法呼吸,眼前阵阵发黑,无数混乱的碎片在脑中炸开——锦衣卫?
冥婚?
活祭品?
三百年前?
这些词如同碎裂的、带着棱角的冰棱,疯狂撞击、切割着残存的意识。
“大人!
大人明察啊!”
地上那个粗嘎声音的汉子像是抓住了最后一根稻草,声音抖得变了调,带着哭腔和浓重的腥臊气,“这……这女子确是陈家买来的‘阴缘人’!
有死契!
有……有血指印为证!
就在……就在陈府管事手里!
小的们……小的们只是奉命行事!
求大人饶命!
饶命啊!”
他磕头如捣蒜,额头撞击腐土发出沉闷的“咚咚”声,每一次撞击都伴随着绝望的呜咽。
死契?
血指印?
我的心沉入无底冰渊。
一张由怨毒、贪婪和冰冷

雾锁冥缘抖音热门小说
推荐指数:10分
现代言情《雾锁冥缘抖音热门小说》,讲述主角抖音热门的爱恨纠葛,作者“外星的牛仔”倾心编著中,本站阅读体验极佳,剧情简介:中元夜大雾,我开车坠入一片明清乱葬岗。腐泥塞满指甲缝时,我摸到颈间绣着“奠”字的鸳鸯荷包。浓雾里传来钉棺材的闷响:“陈家买你配冥婚,子时入棺。” 我踹开棺材板,指着里面那具戴同款荷包的枯骨笑出泪: “三百年前你们陈家骗我殉葬一次了……”“这次轮回,轮到哪位新郎官的后人替祖宗还债?”(开篇:现代公路的......
第8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