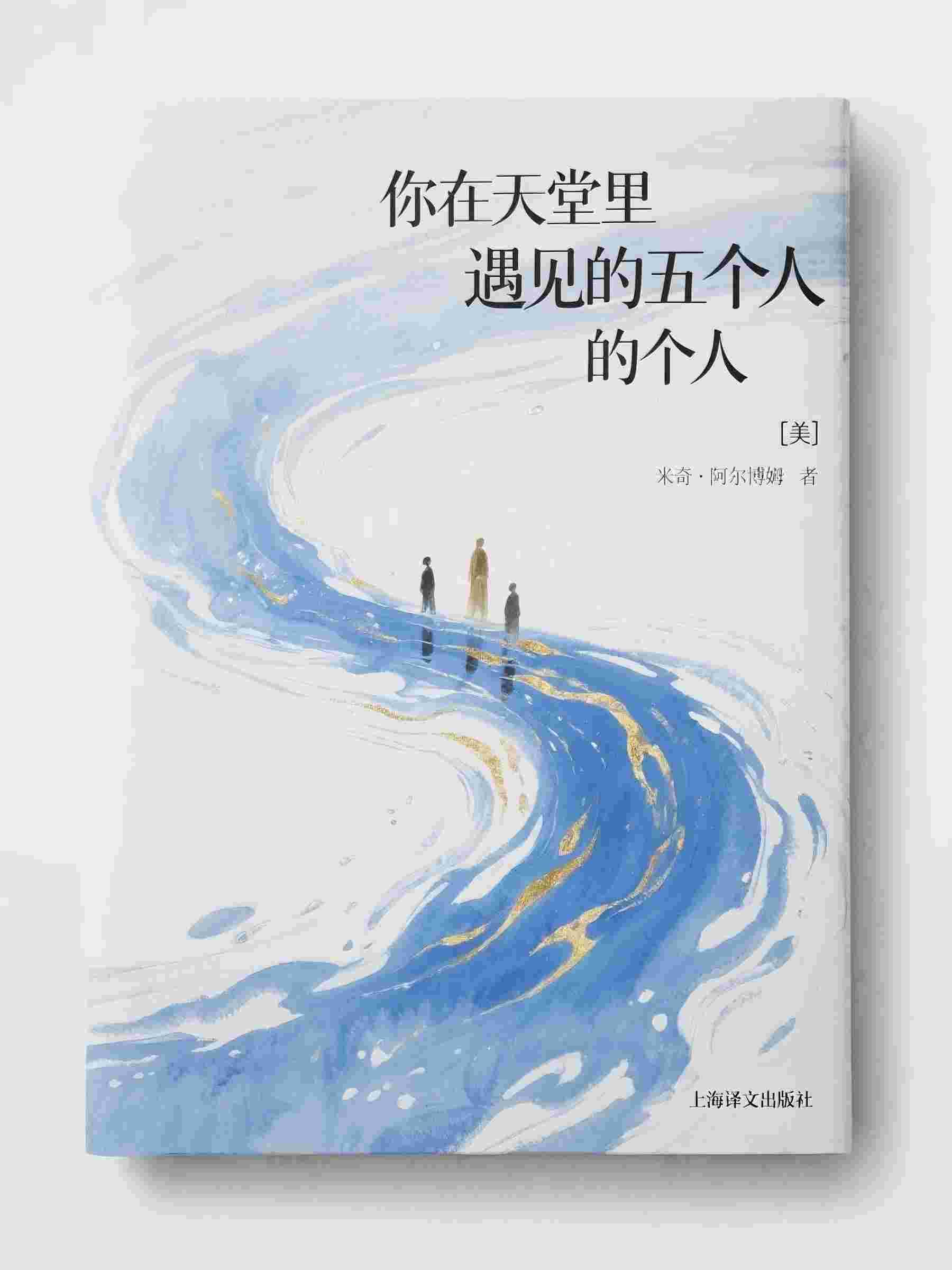缝里抽出鱼尾。
干瘪,僵硬,像枯枝。
就在这时——“当!”
地底传来第二声闷响,像铜钱落地,又像棺盖合拢。
我摊开手掌。
第二道裂痕正在愈合,黑血止住,铜色重现。
视野骤然清明。
走廊外,两名保安经过。
一人头顶浮起黑线,细如发丝,缠绕脖颈。
另一人没有。
楼下街口,穿校服的女孩走过。
她头顶也有黑线,垂落肩头。
我抬头望向大厦对面公寓。
二楼窗口,一个男孩正低头写作业。
他颈间挂着玉佩,蝎纹朝外。
他头顶,黑线如绳,三日内必死。
我刚能见死线,还不稳。
但足够看清谁该下一个。
我收起鱼尾,将罗盘贴回胸口。
风衣口袋里的玉佩发烫,与铜钱共鸣。
我走回通风管,沿原路下楼。
地库里,铜铃依旧悬着,没响。
我经过时,一粒锈渣从铃底掉落,砸在地面。
回到后巷,雨小了。
我靠墙站定,从内袋取出那枚玉佩。
蝎纹在暗处泛青,我用指甲顺着裂痕划过去。
玉佩突然一震,裂开一道细缝。
里面,嵌着半粒黑色骨渣。
我盯着那点残骨,耳边再次响起师父的话:“死子不回头,回头便是局中局。”
我握紧玉佩,指节发白。
这孩子,是不是也死过一次?
玉佩里的骨渣硌着掌心,像一粒烧不化的灰。
我把它按在罗盘背面,血从指缝渗出,滴在铜钱裂口。
裂痕猛地一烫,视野晃了一下,地下那条赤红脉络重新浮现,比之前更清晰,顺着排水渠往东延伸,终点钉在城东高架桥第七墩。
罗盘指针抖得厉害,城市电网像被什么东西搅乱,电流杂音钻进耳膜。
我靠墙站稳,左耳缺角处渗出湿意,不是雨。
那地方二十年前被阴穴咬掉一块肉,现在还在疼。
桥下有几个流浪汉蜷在铁皮棚里。
一个披着破毯子的老头抬头看我:“你也是来看的?”
我没应。
“每晚十一点,桥上走过七个人。”
他咧嘴,牙黑了半口,“穿灰衣,低着头,脚步轻。
走到中间就没了,像被桥吃进去。”
旁边人嗤笑:“又疯说。”
老头不恼,只盯着桥墩:“他们不来找我,我知道。
我不是活人该待的地界。”
我蹲下,掀开排水沟盖板。
水流浑浊,带着铁锈味。
罗盘压在胸口,血继续往上面滴。
三滴后,指针稳住,指向

铜钱裂魂,我执罗盘逆天命无删减+无广告
推荐指数:10分
热门小说《铜钱裂魂,我执罗盘逆天命无删减+无广告》是作者“十八点六”倾心创作,一部非常好看的小说。这本小说的主角是李大富热门,情节引人入胜,非常推荐。主要讲的是:暴雨砸在老宅门槛上,像钉子一排排钉进青石。我睁开眼,跪在门槛内侧,手里攥着半块铜钱。铜绿斑驳,裂成五瓣,嵌进掌心的肉里,黑血顺着指缝往下滴。雨声很大,可我听见了更小的声音——地底深处,传来一声“当”,像是铜钱落地,又像棺材盖合上了。我没死。我回来了。二十年前,我在癸未年五虎遁之日,被师父推入阴穴,成......
第5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