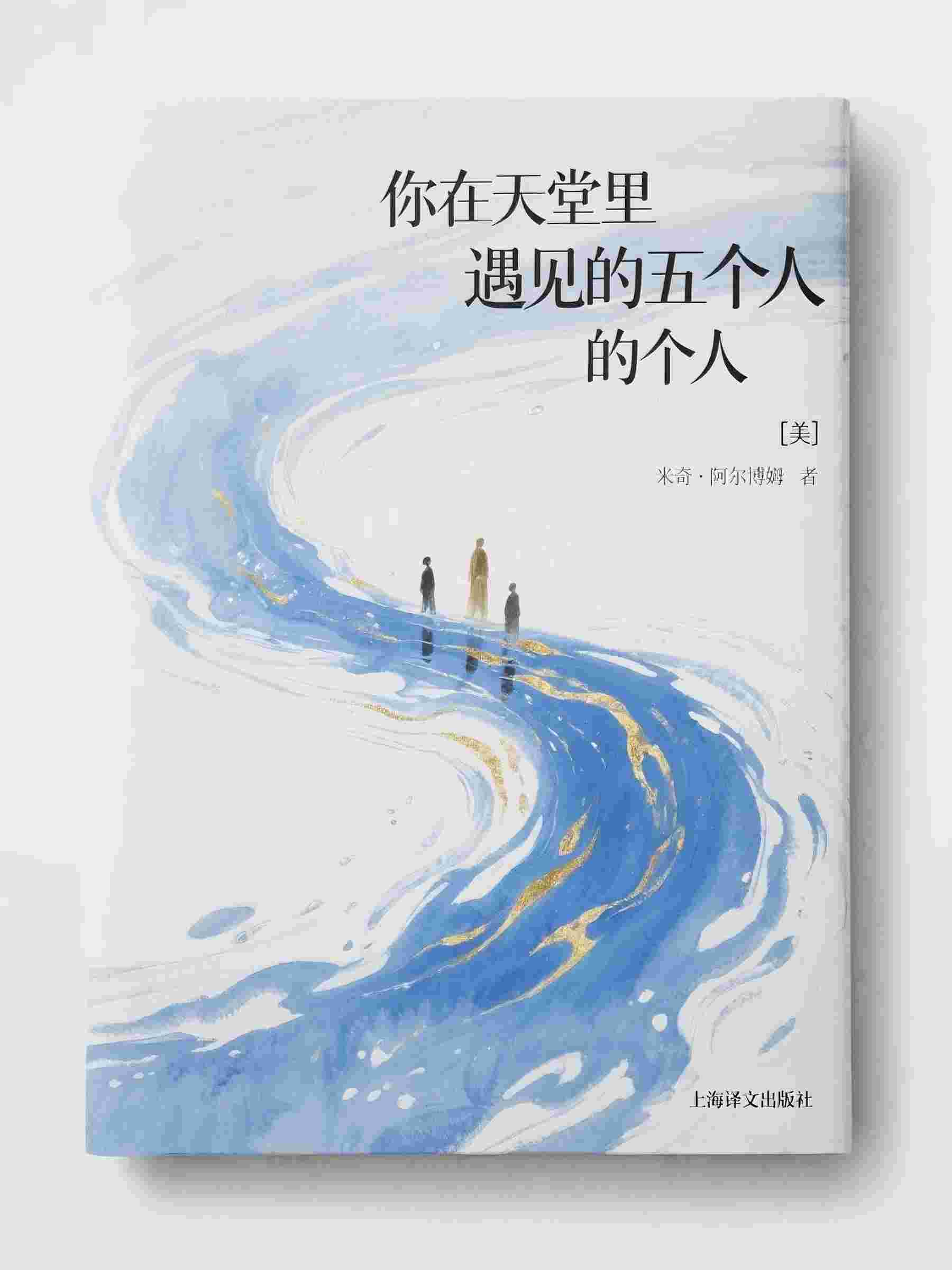吹了吹,送入口中。
温润鲜香的滋味在舌尖弥漫开,是久违的、纯粹的食物的抚慰。
我慢慢地咀嚼着,咽下。
然后,我抬起头,迎上妈妈有些恍惚的视线,声音不大,却清晰地穿透了餐桌上微妙的沉寂:“妈,昨天的溏心蛋……煮得正好。”
话语出口,带着一点生涩,却平稳地落在了空气里。
妈妈拿着筷子的手明显顿住了。
她愕然地看向我,眼神从失焦到震动,嘴唇微微张开,像是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。
随即,那黯淡的眼底,仿佛被投入了一颗小小的石子,极其微弱地波动了一下,有什么湿润的东西迅速弥漫上来,又被她飞快地垂下眼帘强压下去。
她没说话,只是拿起勺子,舀了一勺粥送进嘴里,握着勺柄的手指,指节因为用力而微微泛白。
爸爸喝粥的动作也停了下来,目光在我们之间悄然流转,最后落回自己的碗里,几不可闻地、长长地舒了一口气。
晨光慷慨地铺满了半张餐桌,照亮了碗里那片流淌的金黄,也照亮了妈妈低垂的睫毛上,那一点将落未落的细小水光。
天堂或许依旧遥不可及,地狱的寒意也未曾彻底消散,但我清晰地知道,那束曾被粗暴掐灭的光,已不再是仅仅从缝隙中“漏”进来。
它正以一种微小却执拗的方式,在我心底,在这片曾被言语的寒冰覆盖的土地上,一点一点地,破土生长。
它汲取着每一次磕磕绊绊的尝试,每一次恐惧中伸出的手,每一次笨拙却真实的改变所汇聚的养分。
它还很幼小,带着伤痕累累的印记,但它活着,向上伸展着稚嫩的枝叶,固执地、不容置疑地宣告着存在。

一点一点地,破土成长抖音热门无删减+无广告
推荐指数:10分
主角是抖音热门的精选现代言情《一点一点地,破土成长抖音热门无删减+无广告》,小说作者是“用户名夏光红红火火”,书中精彩内容是:训练营的教室像个巨大的蜂巢,嗡嗡响着别的孩子兴奋的发言。我蜷在角落那把硬邦邦的椅子上,头低得几乎要埋进胸口。刺眼的白炽灯悬在头顶,却照不进我所进的世界。王老师的声音透过嗡嗡声传来,像隔着一层厚厚的水:“这个问题,谁愿意上台来分享?”无数只手争先恐后地举起来,带着迫不及待的劲儿。我的手,却像灌满了沉重......
第12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