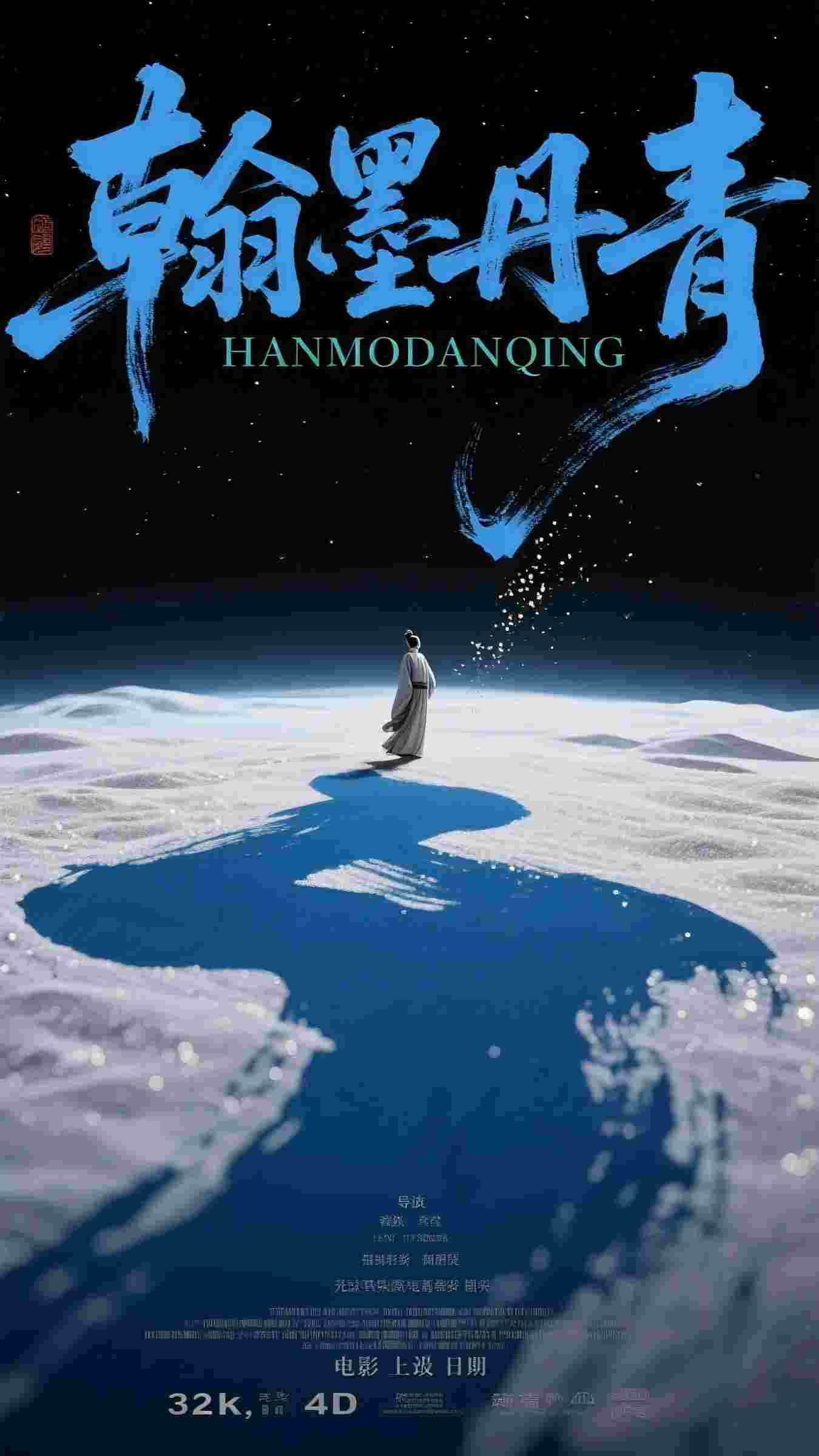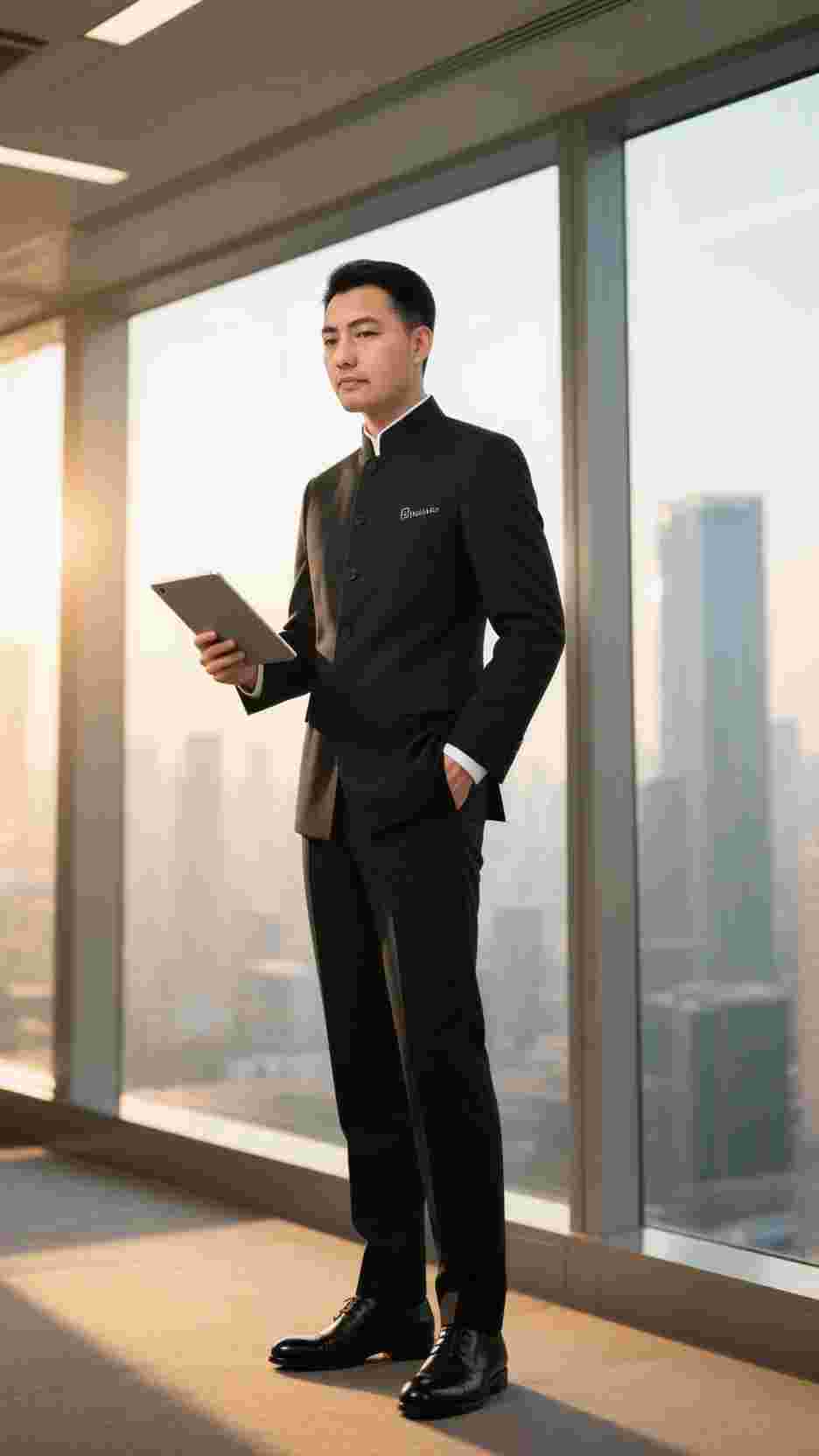最后的光。
而你,却想利用这道光,来照亮你那肮脏悔恨的内心。
你不配。
从那以后,顾渊照再也没有带任何人来见我。
他似乎也放弃了唤醒我记忆的念头。
他只是日复一日地守着我。
喂我吃饭,喂我喝药,给我擦洗身体。
做得那么熟练,那么自然。
他不说爱,也不说恨。
他只是看着我。
用一种我看不懂的,混杂着爱恋、悔恨、痛苦和绝望的眼神,日日夜夜地看着我。
他像一个最虔诚的信徒,守护着自己亲手摧毁的神祇。
他的头发里,开始出现银丝。
他才二十五岁。
正是一个男人最好的年纪。
却已经有了挥之不去的暮气。
有时候,我会在半夜醒来。
看到他坐在床边,就着月光,一笔一划地描摹我的脸。
他的手指,冰凉,颤抖。
不敢真的落下来,只在空中虚虚地画着。
那样子,卑微到了尘埃里。
我曾问过他,为什么要这么做。
在我尚是南楚太子,而他,是来访的北燕少年将军时。
他领兵踏平我故国,将我送入军妓营,又以胜利者的姿态将我“救”出。
这一切,是为什么?
那时,他只是沉默。
如今,他给了我答案。
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夜里。
他从外面进来,带着一身寒气和浓重的血腥味。
他走路的姿势有些不稳,像是刚从一场酷刑中抽身。
他坐在我的床边,替我掖好被角,动作却僵硬得可怕。
“阿絮,”他的声音很轻,却像被砂纸磨过,“我今天……审了一个人。”
我毫无反应。
他自顾自地说下去,像是必须找个人倾诉,哪怕对方是个活死人。
“是军妓营的一个漏网之鱼,屠营的时候,他装死躲过去了。
我把他找了出来。”
他顿了顿,喉结剧烈地滚动了一下。
“我问他,你都经历了什么。”
“他说……他们为了取乐,会把馒头扔在满是污泥的地上,让你像狗一样爬过去捡。”
“他说……他们赌你什么时候会哭,什么时候会求饶。
你越是不出声,他们就越是兴奋。”
顾渊照的声音开始发抖,那是一种从骨头缝里透出来的恐惧和崩溃。
“他还说……打断你腿的那天,是为了给一个新来的校尉看个乐子。
他们拿棍子,一寸,一寸地敲,想听听南楚太子的骨头,断裂的声音是不是比旁人更悦耳……”

断我傲骨后,他说带我回家后续+全文
推荐指数:10分
现代言情《断我傲骨后,他说带我回家后续+全文》,男女主角分别是阿絮顾渊照,作者“心语轻吟”创作的一部优秀男频作品,纯净无弹窗版阅读体验极佳,剧情简介:在发现我是敌国皇子后,他毫不犹豫地将我送进了军妓营。我在那里被折磨得不成人形,成日活在噩梦里。他们打断我的骨头,让我连跪都跪不直。一年后,他平定了我的国家,以胜利者的姿态来见我。他抱着我残破的身躯,颤抖着许诺:“阿絮,战争结束了,我带你回家。以前的事,我们都忘了好不好?”可我低头看着他腰间佩戴的、我......
第8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