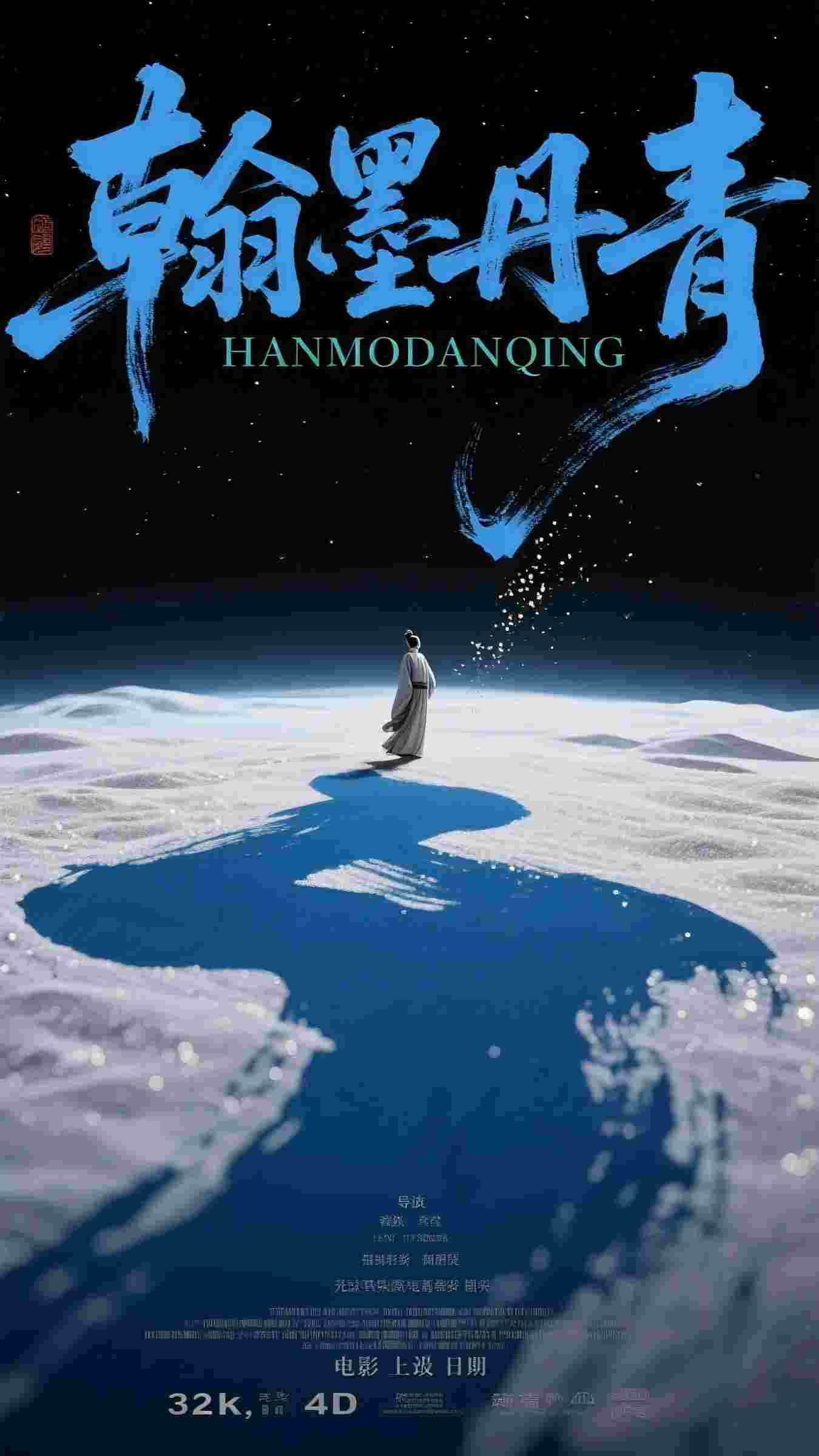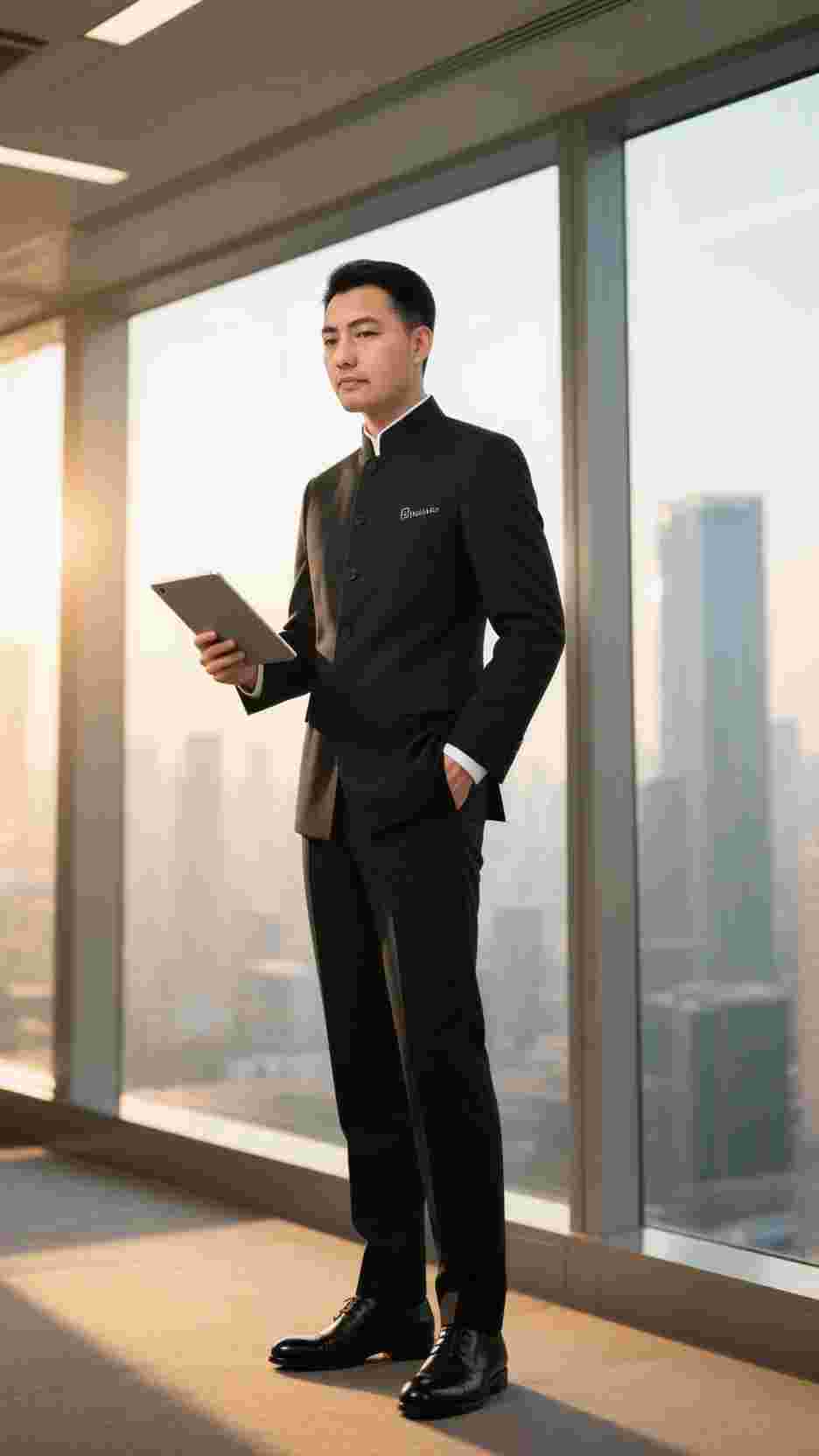一件深灰色的羊绒衫,放入摊开在地上的那个黑色登机箱里。
昏黄的台灯光在他身上投下长长的、孤寂而沉重的影子。
整个空间弥漫着一种无声的、巨大的、令人窒息的悲伤和一种尘埃落定般的决绝。
“沈屿……”我的声音嘶哑得如同破旧的风箱,带着浓重的哭腔和溺水者抓住最后一根稻草般的绝望,“别走……求你……我知道错了……我真的……我不该……” 巨大的羞愧让我语无伦次,“苏晴……我不知道她……” 眼泪汹涌而出,模糊了视线。
我的声音戛然而止。
因为我看见了他放进行李箱的动作。
最后一件深灰色的羊绒衫被小心地放进去,覆盖在衣物上。
然后,他的手并没有离开箱子,而是在箱底摸索了一下。
当他收回手时,指间多了一样小小的东西。
那东西被昏黄的台灯光镀上了一层暖色的光晕,却无法掩盖它本身的陈旧和脆弱——一只纸做的千纸鹤。
纸张早已褪去了原本可能鲜亮的色彩,泛着陈旧的、如同枯叶般的黄褐色,边缘磨损得厉害,甚至有些毛糙卷曲,一只翅膀还带着细微的、被无数次摩挲过的深刻折痕。
它那么小,那么旧,那么不起眼,躺在他宽大的掌心,却像承载着千钧的重量,散发着来自遥远过去的、冰冷的气息。
我的呼吸在那一瞬间彻底停滞!
心脏像是被一只冰冷而熟悉的手狠狠攥住,然后猛地撕裂开来!
尘封的记忆如同开闸的洪水,裹挟着尖锐的、带着锈迹的碎片,轰然冲垮了我摇摇欲坠的理智!
那是我和他刚创立“臻屿设计”不久的时候。
工作室举步维艰,接不到像样的项目,资金链随时可能断裂。
巨大的生存压力和一种莫名的、对沈屿能力的崇拜与依赖交织在一起,让我陷入一种病态的不安。
我害怕他嫌弃我的能力不足,害怕他最终会抛下我和这个烂摊子,去寻找更有实力的伙伴。
一个荒唐又可怕的念头,如同毒蛇般钻入了我的脑海——如果我遭遇了巨大的不幸,他还会不会留下来?
会不会证明他的“义气”足够坚定?
于是,我精心编织了一个谎言。
我告诉他,我母亲突然查出重病,情况很不好,需要巨额医药费,我可能要离开工作室去照顾她…

试探深渊:褪色的纸鹤:全章+后续
推荐指数:10分
现代言情《试探深渊:褪色的纸鹤:全章+后续》是作者““凌霄清黛”诚意出品的一部燃情之作,沈屿苏晴两位主角之间虐恋情深的爱情故事值得细细品读,主要讲述的是:试探深渊:褪色的纸鹤庆功宴上,我发现合伙人沈屿的秘密抽屉上了锁。里面是他发小苏晴的旧手机,每周三他都会独自消失两个小时。闺蜜怂恿我:“试试他,密码就设成你的生日。”手机解锁的瞬间,弹出苏晴憔悴的视频:“阿屿,化疗好痛,但是谢谢你每周送来的汤。”太平间外,沈屿红着眼把死亡证明摔在我脸上:“苏晴死了,现......
第15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