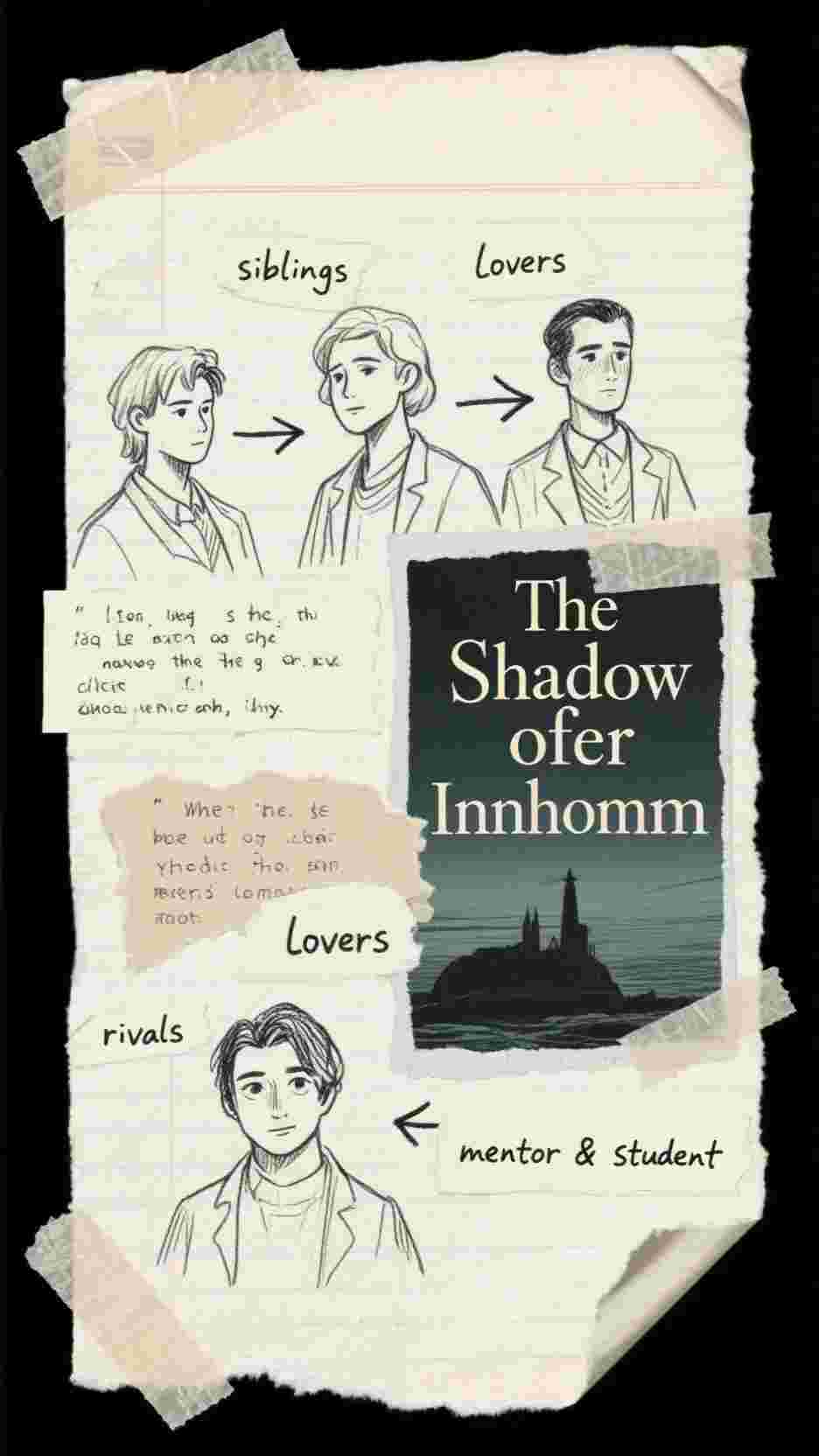破旧的窗纸洞漏进来。
在地上投下一小块惨白的光斑。
我把汤碗放在桌上。
发出轻微的磕碰声。
然后走到床边。
从床板下那个隐秘的缝隙里。
摸出那个小小的布包。
打开。
碎银子。
散钱。
还有那只小小的银镯子。
它们在月光下。
闪着微弱的、清冷的光。
我看着它们。
看了很久。
直到眼睛酸胀。
窗外的桃花香气。
丝丝缕缕地飘进来。
甜得发腻。
又是一年春天了。
我等了三年。
又三年。
桃花开了又谢。
我的平儿。
叫我奶娘。
我的男人。
是别人的夫君。
我柳茵。
是这偌大明府里。
一个没有名字的影子。
一个被亲生儿子遗忘的。
奶娘。
我拿起那只小银镯。
冰凉的触感贴在掌心。
突然。
就不想再闻这桃花的味道了。
***3计划在脑子里慢慢成形。
像黑暗里滋生的藤蔓。
冰冷。
坚韧。
我需要一笔钱。
一笔能让我彻底消失的钱。
明怀瑾每月会给我一点月例。
不多。
勉强够吃饭穿衣。
时悠然管家后。
这点钱也常常被克扣。
名目繁多。
布料涨价了。
府里开销大了。
或者干脆就是忘了。
我攒下的那点碎银子。
加上那只镯子。
远远不够。
我得更仔细地攒。
更隐秘地攒。
我开始接更多的活。
府里没人愿意洗的厚重冬衣。
我洗。
洗得手指冻裂。
渗出血丝。
厨房里最累人的揉面、劈柴。
我来。
揉得腰酸背痛。
劈得虎口震裂。
夜深人静。
别人都睡了。
我点上那盏昏暗的小油灯。
缝补那些管事婆子们丢过来的旧衣破袜。
一针。
一线。
眼睛熬得通红。
换几个可怜的大钱。
有一次。
给府里浆洗房的王婆子缝补她儿子一件扯破的旧棉袄。
针脚歪了。
她尖着嗓子骂我。
说我糟蹋东西。
把棉袄扔到我脸上。
让我赔。
我低着头。
默默捡起来。
拆掉重缝。
熬了大半夜。
眼睛又干又涩。
手指被针扎了好几个洞。
第二天交给她。
她斜着眼看了看。
哼了一声。
丢给我两个铜板。
像打发叫花子。
我默默收下。
攥在手心。
铜板的棱角硌着掌心的裂口。
很疼。
但这疼让我清醒。
钱。
一点点多起来。
藏在我床下那个小小的瓦罐里。
每次放进去。
发出轻微的“叮”一声。
都像是在黑暗里敲响一声微弱的钟。
告诉我。
离自由。
又近了一点点。
离平儿。
却

爱他的我,做了他孩子奶娘明怀瑾明平全文
推荐指数:10分
热门小说《爱他的我,做了他孩子奶娘明怀瑾明平全文》是作者“Timc”倾心创作,一部非常好看的小说。这本小说的主角是明怀瑾明平,情节引人入胜,非常推荐。主要讲的是:1我蹲在灶房冰冷的地上。用力擦着那口油腻的大铁锅。锅底积着厚厚的黑灰。水很冷。手指冻得通红,有点发僵。门外传来一阵喧闹。吹吹打打的声音。像针一样扎进耳朵里。我知道,是明怀瑾回来了。带着他的新夫人。那个叫时悠然的女人。八抬大轿,风风光光。我低着头。继续擦锅。锅沿一处顽固的油渍,怎么也擦不掉。就像我此刻......
第5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