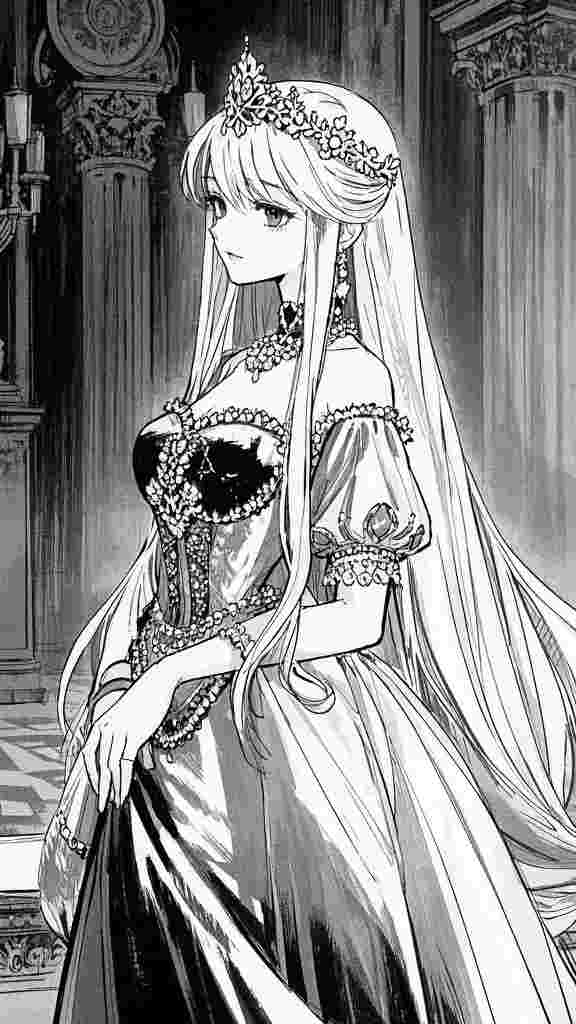胃药,指关节因为过度用力而泛出青白。
那张总是带着几分玩世不恭笑意的脸,此刻只剩下一种彻底的、死灰般的冰冷。
所有的表情都消失了,肌肉僵硬得像一块雕刻失败的石膏。
只有那双眼睛。
那双刚才还因为胃痛而泛着生理性泪光、此刻却如同两口结了厚厚冰层的深潭的眼睛,死死地、一瞬不瞬地钉在我脸上。
那眼神里,没有震惊,没有恐惧,没有愤怒,甚至没有一丝一毫的疑问。
只有一片望不到底的、令人骨髓发寒的洞悉和……冰冷的死寂。
仿佛刚才那句“处理掉你的配偶季霄”的指令,并非只在我的耳机里响起,而是同样清晰地、一字不落地,直接灌入了他的耳中。
空气里最后一丝稀薄的热气也被抽干了,只剩下绝对的零度,冻结着每一个微小的尘埃。
他看着我。
那空洞冰冷的目光,穿透了我脸上可能残存的任何一丝惊愕或伪装,直抵某个最核心、最残酷的真相。
然后,他动了。
极其缓慢地,季霄那只没有拿药瓶的手,一点一点地抬了起来。
他的动作僵硬得如同生锈的提线木偶,带着一种令人窒息的迟滞感。
那只手,越过散落一地的杂物,最终,停留在那本摊开的、印着两人照片和名字的深红色结婚证上方。
他的食指和中指,如同冰冷的镊子,精准地夹住了那本薄薄的、却重逾千斤的证件。
然后,以一种缓慢到近乎仪式化的速度,将它从地上拾起。
深红色的硬壳封面,在昏暗的光线下像一块凝固的血痂。
他举着它。
手臂抬到与胸口平齐的位置,停住。
那本小小的证件,像一面宣告终结的旗帜,又像一纸无声的控诉状,横亘在我们之间狭窄而致命的空气里。
他的喉结,极其艰难地上下滚动了一下。
干裂的嘴唇微微翕动,发出的声音不再是之前的尖利质问,而是低沉、沙哑、平滑得像冰面下缓慢流动的寒流,每一个字都带着足以冻结灵魂的重量:“原来……”季霄的声音顿了顿,那双冰封的眼眸深处,似乎有什么极其锐利、极其黑暗的东西,刺破了表面的死寂,一闪而逝。
“你要‘处理’的人……”他的嘴角极其缓慢地向上扯动了一下,形成一个完全没有任何温度、甚至称不上是
老公他任务目标竟是我后续+番外 第9章 试读
用户24831453 著 季霄热门现代言情 来源:cddp 时间:2025-08-15 22:23:42

老公他任务目标竟是我后续+番外
推荐指数:10分
《老公他任务目标竟是我后续+番外》,是网络作家“季霄热门”倾力打造的一本现代言情,目前正在火热更新中,小说内容概括:我和黑客季霄被迫合租两年,从互相嫌弃到学会照顾对方。他总笑我像个老妈子,却会默默吃掉我煮糊的粥。直到我执行任务重伤回家,他慌乱翻找药箱时碰落抽屉。“沈默!为什么结婚证上有我们照片?日期还是三年前?”我盯着他手中的红本,通讯器突然震动。上司冰冷指令传来:“目标已确认,立即处理掉你的配偶季霄。”季霄举着......
第9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