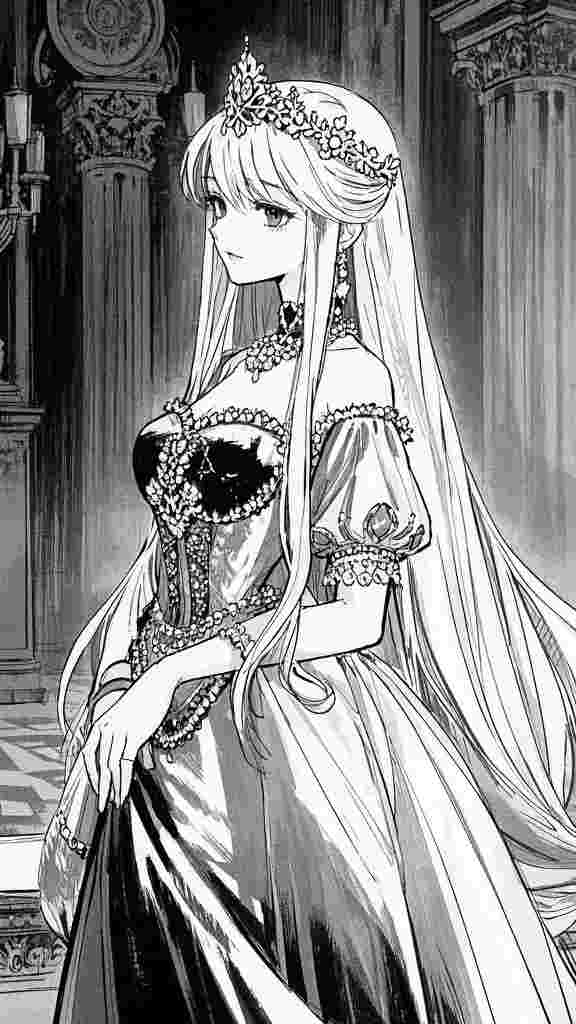里落进细小的沙粒,她也不在意。
她绣得最多的是海,是陈屿的船,是夕阳下归航的桅杆,绣着绣着,就把陈屿的影子也绣了进去——他赤着脚在滩涂奔跑,裤脚卷到膝盖,脚踝沾着泥,却笑得比阳光还亮。
变故来得像场突如其来的台风。
那天陈屿出海时,天气还好好的,中午突然起了风暴,海浪像发怒的野兽,把渔船掀得东倒西歪。
渔村的人都站在岸边,看着黑沉沉的海面,没人说话,只有风声像哭。
林未的手死死攥着刚绣了一半的船帆,指节发白。
母亲在她身边发抖,反复念着“没事的,陈屿水性好”,可声音里的恐惧骗不了人。
直到后半夜,风暴才停。
远处的海面上漂着些碎木板,是陈屿的船。
林未疯了似的往滩涂跑,礁石划破了她的脚,血珠滴在沙地上,很快被海水冲散。
她看见几个渔民抬着个人往回走,蓝衬衫被海水泡得发胀,正是陈屿。
“陈屿!”
她扑过去,手指触到他的皮肤,凉得像冰。
“还有气!
快送医!”
有人喊。
陈屿昏迷了三天三夜。
医生说他断了两根肋骨,肺部进了水,能不能醒,要看他自己的求生意志。
林未守在他床边,给他擦手,给他讲他们还没绣完的船帆,讲母亲新腌的鱼干,讲滩涂上刚冒出来的小螃蟹。
“你说过要带我看退潮的礁石,”她握着他冰凉的手,眼泪掉在他手背上,“你不能说话不算数。”
第四天早上,陈屿的手指动了动。
林未猛地抬头,看见他睫毛颤了颤,睁开眼,声音哑得像砂纸摩擦:“船……船没了?”
“船不重要,”林未扑到他怀里,哭得像个孩子,“你回来就好。”
陈屿的船真的没了。
那是他父亲留下的老船,陪他在海上漂了十几年。
他醒来后,沉默了很久,每天坐在窗边看海,眼神空得像退潮后的滩涂。
林未知道他在想什么。
她把那幅绣了一半的船帆找出来,坐在他床边,继续绣。
“我们可以再做一艘,”她穿好线,针尖在布上落下,“你劈木头,我来绣船帆,就像我们在老城区那样。”
陈屿没说话,只是看着她的针在布上游走,把破碎的船帆一点点补完整,添上桅杆,添上渔网,添上远处的海鸥。
“你看,”林未把绣好的船

青瓦与海风完结+番外
推荐指数:10分
现代言情《青瓦与海风完结+番外》,由网络作家“月月的粘人精”所著,男女主角分别是林未林未没,纯净无弹窗版故事内容,跟随小编一起来阅读吧!详情介绍:林未第一次见到陈屿,是在台风过境的午后。她蹲在老城区的青瓦下躲雨,怀里抱着刚收的绣品,雨水顺着屋檐的凹槽往下淌,在青石板上砸出细密的坑。忽然有辆半旧的摩托车“吱呀”一声停在旁边,溅起的水花差点打湿她的绣绷,骑车的人摘下头盔,发梢的水珠甩了她一脸。“对不住。”男人的声音混着雨声,有点哑,却带着股海风的......
第7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