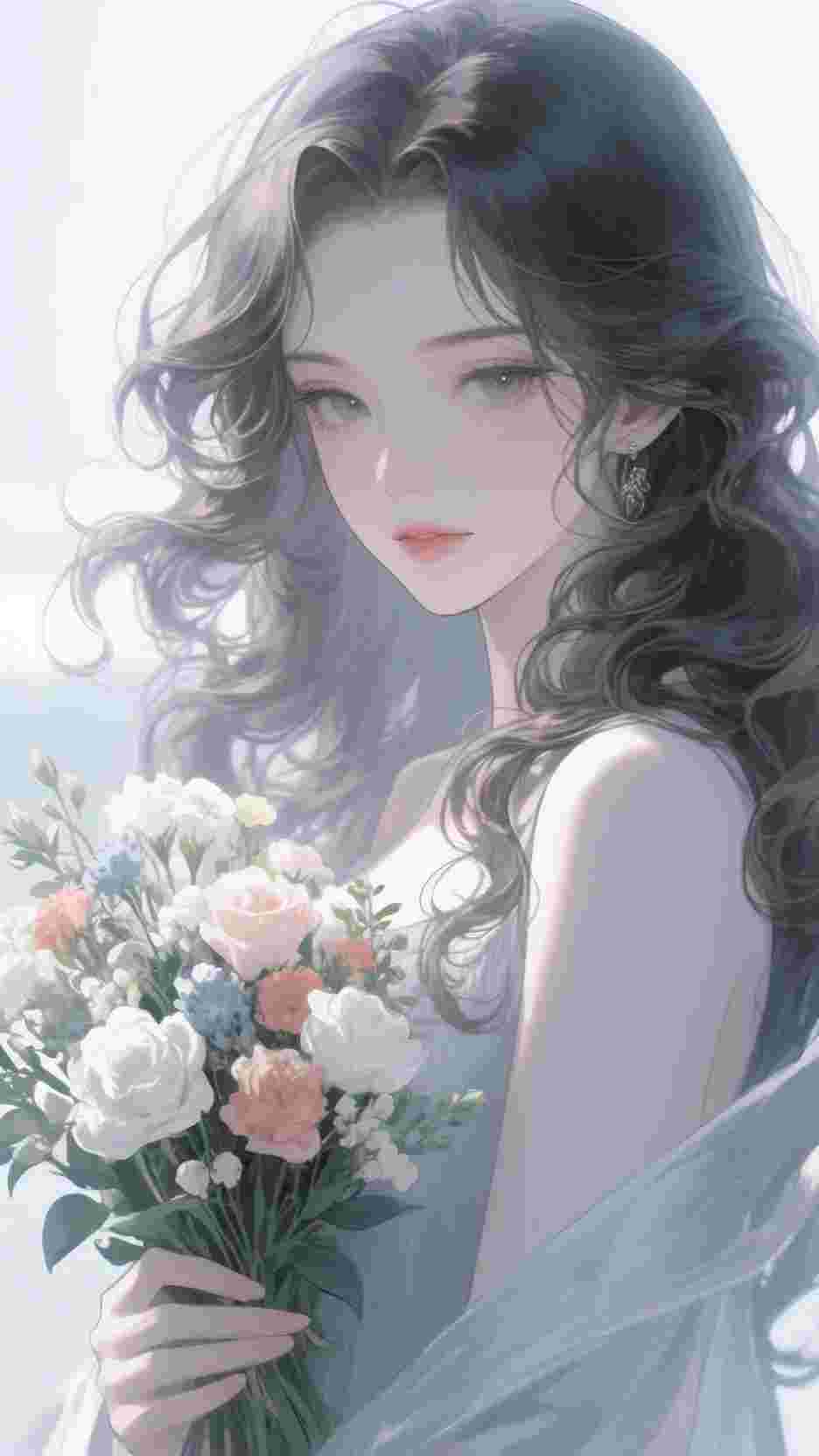……”钥匙插进锁孔,转了半圈卡住了。
我低头看着锁芯里的锈迹,像看着这些年磨出的茧:“这房子换锁了。”
他的脸瞬间垮下去,水果篮“啪”地掉在地上,苹果滚得满地都是。
有个滚到我脚边,我抬脚躲开,鞋跟碾过一片干枯的菊瓣——是早上从公园带回来的。
“你走吧。”
我推开家门,妈先一步迈进去,背影挺得笔直,“这房子装不下那么多人的心思。”
关门前,我看见他蹲在地上捡苹果,西装裤的膝盖处磨出了个洞。
楼道里的声控灯灭了,他的影子陷在黑暗里,像团被揉皱的废纸。
屋里,妈正往花瓶里插菊花。
她踮着脚够橱柜上的花瓶,动作比上次利索多了。
“这花开得真好。”
她转过身,鼻尖沾了点黄色的花粉,“比他带来的那些强。”
我走过去帮她扶着花瓶,阳光从阳台涌进来,把我们的影子投在墙上,像幅熨帖的画。
茶几上摆着刚蒸的南瓜饼,是妈早上五点起来做的,甜香混着菊香漫开来,把整个屋子都泡得暖暖的。
“下周带你去买金镯子。”
我咬了口南瓜饼,糖馅烫得舌尖发麻,“爸当年没给你买的,我给你补上。”
妈手里的菊花枝晃了晃,黄色的花瓣落在她的枣红外套上:“瞎花钱……”话没说完,眼泪就掉在花瓣上,像颗晶莹的露珠。
夜里起夜,看见妈房间的灯还亮着。
我轻轻推开门,她正坐在床边,手里摩挲着那件藏蓝色的毛衣——是去年给老公织的,一直没送出去。
月光从窗帘缝钻进来,在毛衣上织出层银霜。
“睡不着?”
我走过去坐在她身边。
她把毛衣叠起来,放进床头柜的抽屉:“老了,觉少。”
抽屉里露出半截红布,是她的存折本,“明天把这钱存成你的名字吧。”
“您自己留着。”
我按住她的手,“您的钱,自己花才舒心。”
她看着我,突然笑了:“还是闺女好。”
关上门的瞬间,客厅的挂钟敲了十二下。
我望着窗外的月亮,突然想起领证那天,老公说“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”。
原来有些家人,不是靠红本本捆在一起的,是靠一碗热汤、一件毛衣、一句“我给你撑腰”慢慢焐热的。
第二天早上,妈煎了我爱吃的糖心蛋。
阳光透过厨房的窗户,在她

陪嫁房里的逐客令你妈走我爹妈住全文+番外
推荐指数:10分
精品现代言情《陪嫁房里的逐客令你妈走我爹妈住全文+番外》,赶快加入收藏夹吧!主角是陈莉热门,是作者大神“兔窝窝”出品的,简介如下:楔子客厅的水晶灯还亮着,妈刚把洗好的草莓放进果盘,防盗门就被人用钥匙拧得“咔嗒”响。老公撞进来时,公文包砸在茶几上,果盘里的草莓滚了一地,红得像溅落的血珠。“给你妈收拾东西。”他扯掉领带,声音像淬了冰,“我爹妈后天到,让她两天内搬走。”妈手里的玻璃碗“哐当”掉在地上,碎片混着草莓汁溅到她的布鞋上。我......
第8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