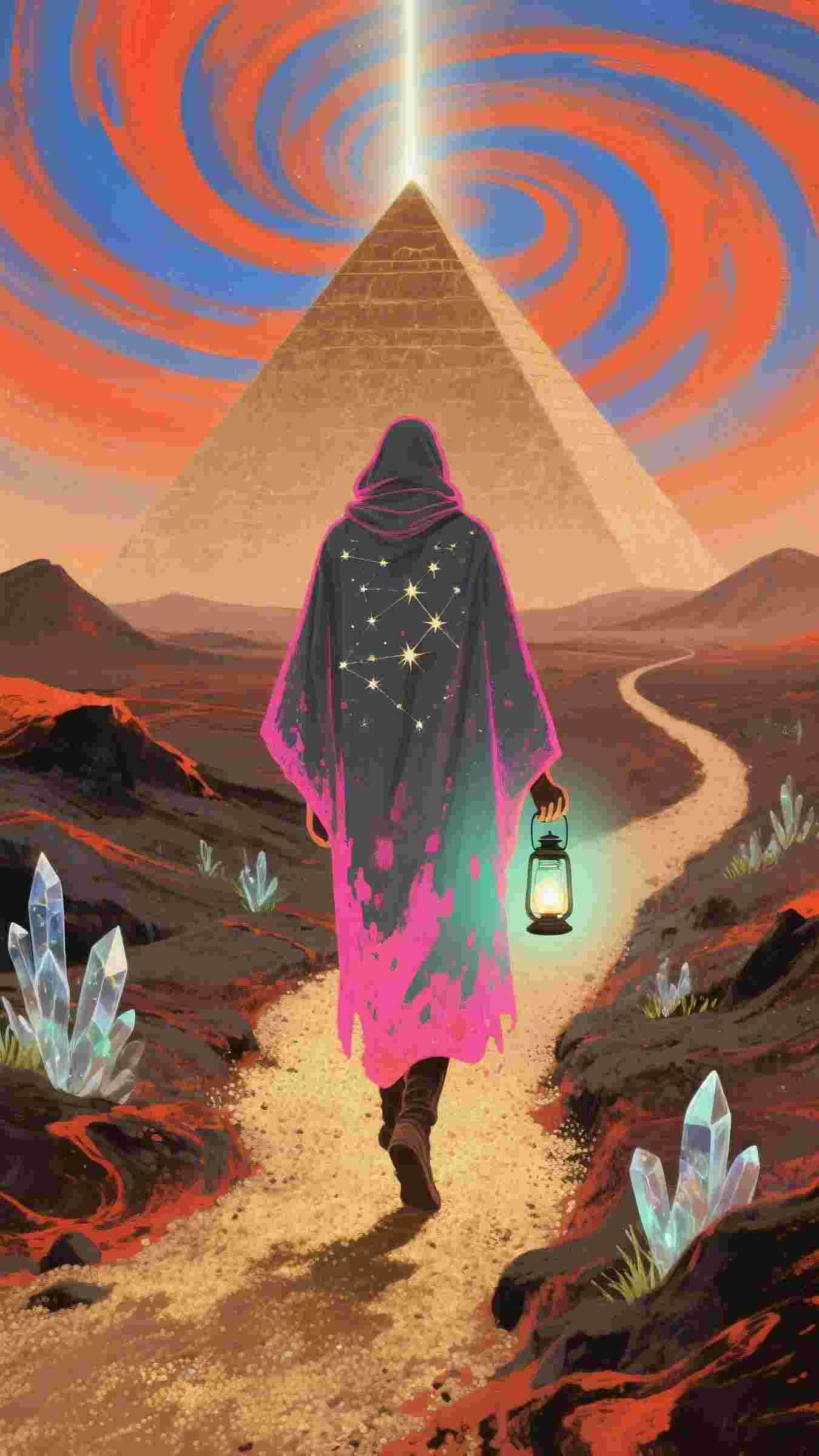的钢丝,一圈圈地勒住我的喉咙。
而这个窒息感,终于在某天晚上,达到顶峰。
那天晚上,我和她去参加王磊的生日聚会。
在一个装修温馨的小酒吧里,灯光昏暗,音乐轻柔。
王磊、他的女友,还有几个我们共同的朋友都在。
他们都冲我笑,那种真诚的,又带着一点点……了然的笑容。
“最近气色好多了啊,”王磊端着酒杯走过来,轻轻碰了碰我的杯子,“听小雅说,你最近状态挺好的,她也放心多了。”
他提到“小雅”的时候,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我女朋友的方向。
我女朋友正在和王磊的女友开心地聊着什么,笑得花枝乱颤。
他们是在告诉我,他们都知道我“之前不对劲”,现在“好多了”。
我心里像被针扎了一下。
“嗯,是啊,”我干巴巴地回答,握着酒杯的手指开始发抖,“最近工作也辞了,是清闲了不少。”
“是该好好休息,”王磊拍了拍我的肩膀,语气带着一丝安抚,“咱们这些年轻牛马啊,偶尔压力大了,总会有点负能量。
没事,调整好了就行。”
他身边的几个朋友,也走了过来,一个个地跟我说着类似的话。
“对啊,李卫,男人嘛,压力谁都有。”
“你看着是好多了,以前总皱着眉。”
“小雅昨天还跟我说,你最近总算是开朗起来了。”
他们的脸上都带着善意的笑容,那种对“我”的理解和接纳。
他们看我的眼神,就像在看一个曾经陷入妄想,如今终于“回归正常”的病人。
我放弃了。
我还能做什么呢?
这些,都只会被当成我病情加重的症状。
我点了点头。
宴会结束后,我像一个提线木偶,跟着她走出酒吧,坐进车里。
车窗外,城市的霓虹完美地闪烁着。
没有坏掉的灯牌,没有乱停的车辆,一切都井然有序。
我靠在座位上,看着身边小雅完美的侧脸。
她一边开车,一边用余光担忧地看着我。
我忽然意识到,这个世界修正的,可能不是那些“破损”的物件或“错误”的记忆。
它修正的,是我。
他们不是在同化我,他们是在“治愈”我。
车子平稳地行驶在干净的街道上。
我闭上了眼睛,感到一阵前所未有的、深入骨髓的疲惫。
也许,睡一觉,真的会好吧。
也许明天醒来,我
昨天,我摔碎了女友的玻璃熊:全本+番外+后续 第8章 试读
原来讨口子这么容易呀 著 抖音热门现代言情 来源:cddp 时间:2025-08-17 01:22:38

昨天,我摔碎了女友的玻璃熊:全本+番外+后续
推荐指数:10分
经典力作《昨天,我摔碎了女友的玻璃熊:全本+番外+后续》,目前爆火中!主要人物有抖音热门,由作者“原来讨口子这么容易呀”独家倾力创作,故事简介如下:1、那东西碎掉的声音,我现在都记得。很脆,像是冬天清晨第一层薄冰被踩裂的声音。啪的一声,然后是极细微的、玻璃渣滚在地板上的沙沙声。我和她吵架了。为了什么?忘了,真的忘了。可能是晚饭吃什么,也可能是谁该去倒垃圾。这种屁事,堆积起来,就能把人点着。我记得我当时吼了一句什么,情绪上头,手臂挥了一下,手背磕......
第8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