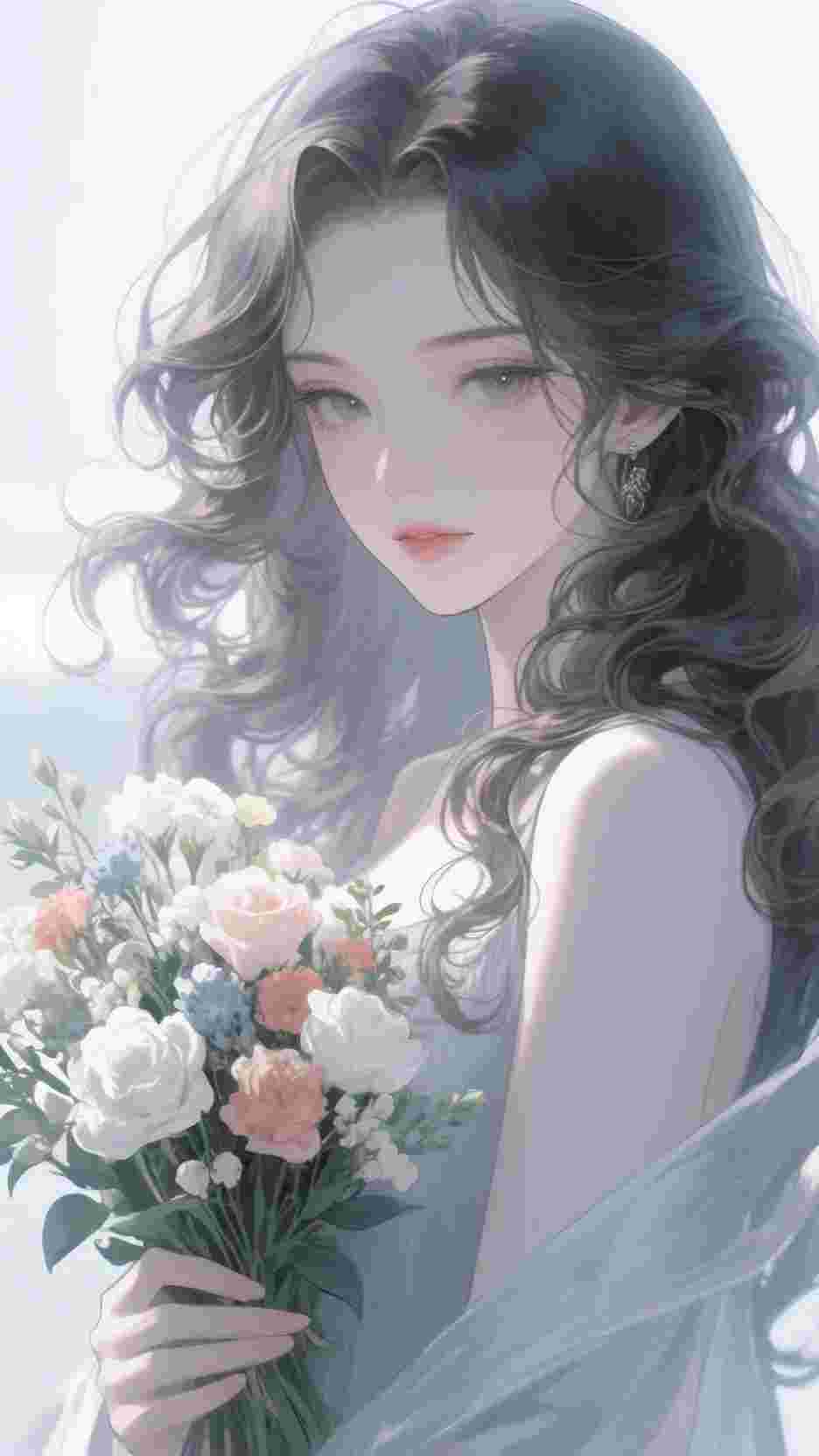负的小孩:“我在泥土里待了二十五年,冷得连骨头都疼,你就不能让我出来透透气吗?”
哭声刚落,阁楼的铜镜突然 “哐当” 一声巨响,震得堂屋的窗棂都跟着颤。
从窗缝里涌出来的灰雾裹着无数根黑头发,像群疯了的虫子,密密麻麻朝着八仙桌扑过来。
我刚想往后躲,手背上的咒痕突然传来一阵剧痛 —— 不是之前的刺痛,是像有把细刀在顺着花纹割皮肤,疼得我 “嘶” 地吸了口冷气,低头一看,灰液竟开始往皮肤里渗,渗过的地方又麻又僵,像冻住了,连手指都蜷不起来。
“别躲了。”
阿棠的声音从灰雾里钻出来,雾团慢慢聚成人形 —— 是她穿蓝布衫的样子,头发垂在胸前,发梢还沾着湿泥,一甩头就往下掉渣,左眼的黑洞里不断流出灰液,顺着下巴滴在青石板上,没留下痕迹,却让地面的青苔瞬间变成了死灰色,像被吸走了所有生气。
她手里攥着那把缺齿木梳,梳齿上缠着几缕黑头发 —— 我一眼就认出,是我早上梳头时掉的,她一甩梳子,头发就像鞭子般朝我抽过来,带着股腥气:“你外婆把我的头发缠在镜腿上时,也是这么用力,她说‘阿棠乖,梳完头就能见妈妈了’—— 可我见到的,是河里的冷⽔,是能冻住骨头的水!”
头发鞭子抽过来的瞬间,我慌忙往后退,后背 “咚” 地撞在墙上,疼得我眼前发黑。
墙上挂着的外婆画像突然 “哗啦” 掉下来,画框摔在地上裂成两半,画像里的墨眼竟慢慢变成了两个黑洞,和阿棠的左眼一模一样,黑洞里流出灰液,顺着画纸往下滴,在地上汇成个小小的水洼。
水洼里映出的不是我,是母亲的脸 —— 她躺在医院的病床上,身上裹着层灰雾,嘴唇紫得像茄子,气息微弱地对着我摇头:“知夏,别管我…… 快跑……你看,你妈快不行了。”
阿棠的人影往我这边飘了飘,灰雾裹着她的衣角,像有无数只无形的手在拉她,让她的身形忽明忽暗。
她手里的木梳突然指向八仙桌下的蓝布包,布包的绳结 “啪” 地就开了,阿棠的尸骨滚出来,那根细细的指骨朝着我的方向伸,手腕上缠着的蓝布带(当年

梳魂债抖音热门(番外)+(全文)
推荐指数:10分
现代言情《梳魂债抖音热门(番外)+(全文)》是作者““鏵鐤”诚意出品的一部燃情之作,抖音热门两位主角之间虐恋情深的爱情故事值得细细品读,主要讲述的是:第一幕:归乡・老宅的镜中影长途汽车在盘山公路上晃了六个小时,最后停在古镇入口那棵歪脖子老槐树下时,我攥着背包带的手已经浸了汗。风裹着雨丝扑过来,混着股说不清的味道 —— 是天井青苔的腥气,是纸钱燃尽的焦糊味,还有一缕极淡的玫瑰胭脂香,像有人刚从民国的旧画里走出来,擦过我的鼻尖。“知夏?” 村长的声音......
第16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