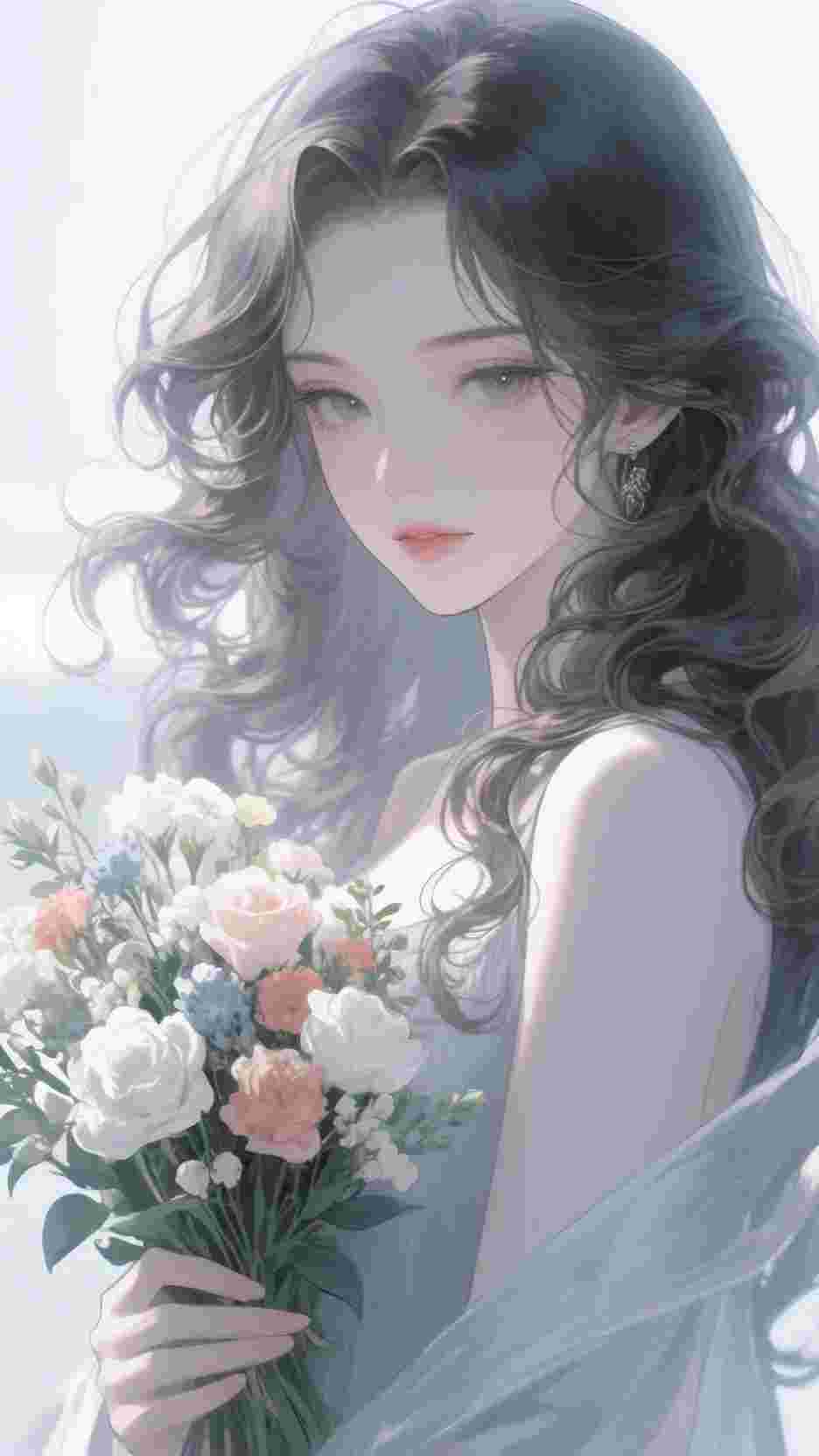。
“林穗?”
她的额头烫得吓人,像是被什么魇住了,反复念叨着“赚钱重要”、“别做梦了”。
那些是我当年说过的话。
在她兴奋地规划科考路线时,我正被叔伯逼着算港口扩建的成本,回头就说了句“你的研究能填公司的窟窿吗”。
我蹲在她面前,声音发涩,“以前我说过很过分的话,对不起。”
她慢慢抬起头,眼泪糊了满脸。
“你是谁?”
“我是想弥补过错的人。”
我艰难地回答。
她没再问,把脸埋进膝盖里,低声呜咽。
第二天我去镇上买退烧药,回来时远远看见苏曼正往林穗的水杯里倒东西。
林穗刚端起杯子要喝。
“别喝!”
我一把打翻水杯,水洒在她的笔记本上,晕开一小片墨迹。
苏曼吓得后退一步,药瓶掉在地上滚到我脚边。
标签上写着“镇静剂”。
“周屿你疯了!”
她强装镇定,“我看穗穗不舒服,给她加点安神的药。”
“是吗?”
我掏出手机按下110三个数字,“还要我把警察叫来,看看这东西是安神的吗?”
她的脸瞬间白了,指着林穗骂:“都是你!
要不是你,我早就跟周屿在一起了!”
“让她走。”
林穗突然开口,手里紧紧攥着那本湿了的笔记本,眼神冷得像冰。
我拽着苏曼的胳膊往外拖,她一路骂骂咧咧:“周屿,你会后悔的!”
关上门转身时,林穗正蹲在地上捡玻璃碎片。
“别动。”
我扑过去抓住她的手腕,看到她指尖被划了道小口,血珠正往外冒。
她看着我,忽然说:“那个‘他’,是不是总让你难过?”
我低头用创可贴包好她的手指,声音很轻。
“是我让他难过。”
11码头竞拍会上,江辰坐在第一排,眼神中充满得意。
“五百万。”
他又一次加价,声音不大,却像重锤敲在会场每个人心上。
旁边的律师拽了拽我的胳膊:“周总,账户里的钱最多只能加到四百八十万。”
“六百万。”
我虚张声势再次加价。
“六百五十万。”
江辰的声音带着笑,“周总不跟了?
这可是你父亲一手建起来的码头。”
三伯故意提高声音:“家门不幸啊,为了个女人连祖业都不要了。”
我突然站起来大声说,“我放弃竞价,但我有件事宣布。”
江辰的笑容僵住了,酒杯停在嘴

旧票随浪去,新程向海开林穗江辰:结局+番外+完结
推荐指数:10分
最具实力派作家“疯语”又一新作《旧票随浪去,新程向海开林穗江辰:结局+番外+完结》,受到广大书友的一致好评,该小说里的主要人物是林穗江辰,小说简介:林穗把船票递过来,“我们说好的,环球航行。”“别闹了,我们不合适。”我狠心把船票撕成碎片。她弯腰捡起碎片,转身离开,哭得肩膀一抽一抽的。江辰说道:“这是明智的选择。”我突然冲进洗手间干呕,镜子里的眼眶红得吓人。1签完港口扩建合同,才有空看林穗的信息:“船票我买好了,下周的科考结束就出发,等你。”我点......
第8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