轻蔑的漠视,而是混杂着深入骨髓的恐惧和一种毒蛇般的阴冷怨毒。
每次狭路相逢,他都像被烫到一样猛地低下头,佝偻着背匆匆躲开,但招娣总能感觉到那两道黏腻冰冷的视线,如同跗骨之蛆,死死钉在自己背上。
她知道,这老东西在等,等一个能把她彻底踩死、夺回那半本邪书的机会。
他也在怕,怕那晚的事被她捅出去。
空气里弥漫着一种无形的、令人窒息的张力。
招娣感觉自己像走在一条架在深渊上的独木桥,两边都是张开血盆大口的猛兽。
怀里的邪书沉甸甸的,像一块烧红的烙铁,也像一把淬了毒的匕首。
这天傍晚,残阳如血,泼洒在贫瘠的山坳上,给枯井冰冷的青石井沿也染上了一层不祥的暗红。
招娣挎着破篮子,假装在井边荒地挖野菜。
她眼角的余光,死死锁在不远处老王头家那扇紧闭的院门上。
门,“吱呀”一声开了。
老王头佝偻的身影闪了出来,他紧张地左右张望,确认无人注意后,脚步飞快,却不是往家走,而是径直朝着村西头——马寡妇家的方向!
招娣的心猛地一紧,一股冰冷的预感攫住了她。
她立刻丢下篮子,像只矫健的狸猫,借着沟坎和矮墙的掩护,悄无声息地跟了上去。
老王头没有直接去马寡妇家,而是鬼鬼祟祟地绕到了屋后那片废弃的碾房后面。
那里,一个微胖的身影早已在阴影里等候多时——正是村长!
“怎么样?
老王!”
村长的声音压得很低,却掩不住那股急不可耐的兴奋,“那草人……有十天了吧?
马春兰那婆娘,是不是快成了?”
他搓着手,脸上泛着油光,眼睛里闪烁着淫邪的光。
老王头那张枯树皮似的脸在阴影里挤出一个谄媚又诡异的笑容:“嘿嘿,村长大人,您放心!
她那魂儿,早就被井里的‘东西’勾得差不多了,再加上枕头上那草人日夜熬着她……”他凑近了些,声音压得更低,带着一种邀功的得意,“我估摸着,就这两天!
保管叫她神志不清,您想怎么‘照顾’她都成!”
“好!
好!”
村长激动得脸上的肥肉都在抖,他重重拍着老王头的肩膀,“事成之后,那两亩地,立马划给你!”
“谢村长!
谢村长!”
老王头点头哈腰,浑浊的三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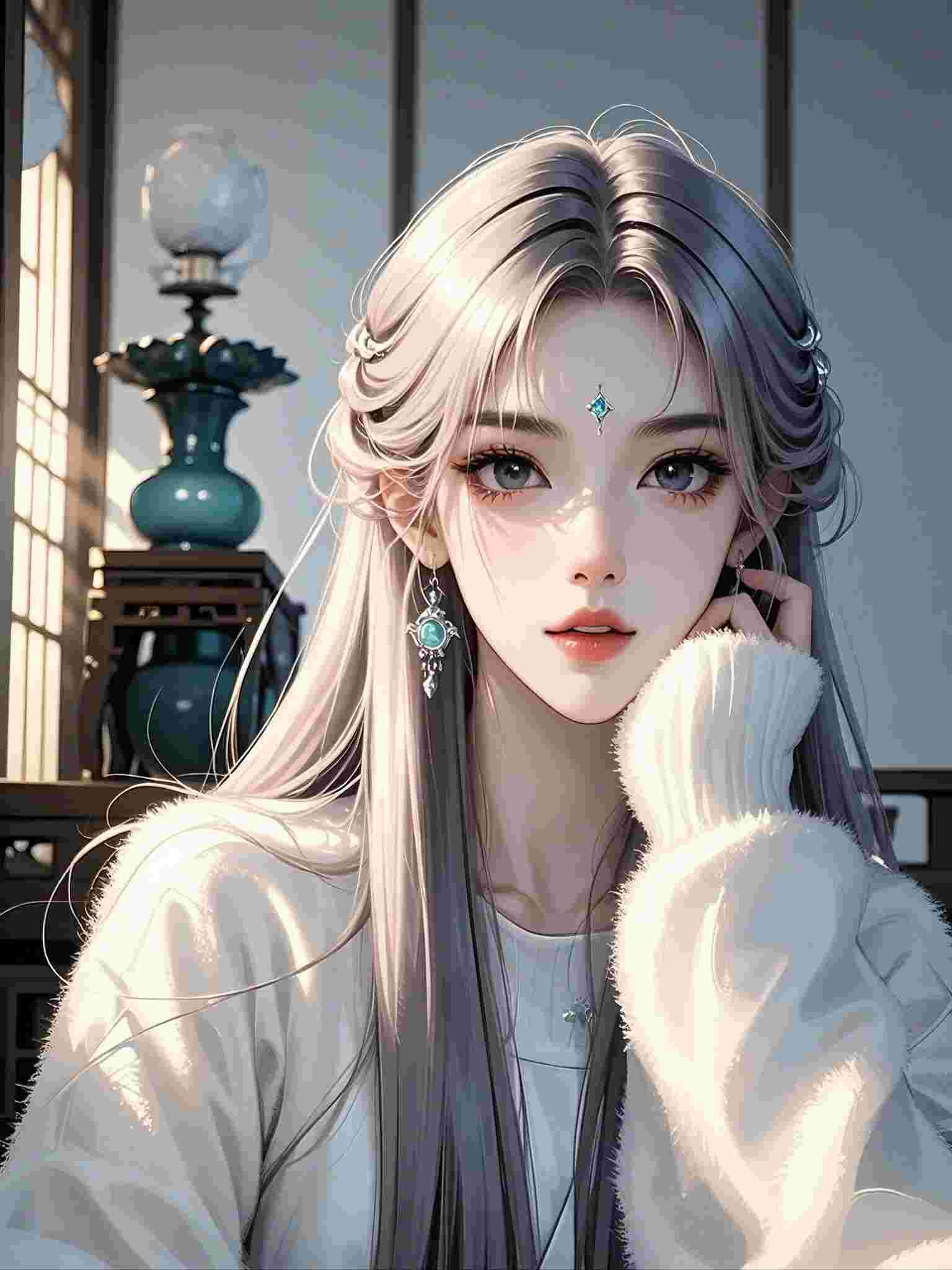
八字纯阳的招娣老王头张招娣小说结局
推荐指数:10分
老王头张招娣是《八字纯阳的招娣老王头张招娣小说结局》中的主要人物,在这个故事中“赚钱”充分发挥想象,将每一个人物描绘的都很成功,而且故事精彩有创意,以下是内容概括:十三岁那年,张招娣在淹死过人的枯井边挨骂。弟弟天赐突然指着井口说:“姐姐,井里有东西哭。”当夜,她尾随会鲁班术的老王头来到马寡妇家。在窗缝里,她看见老王头将写着生辰的草人塞进枕头。“一个月内,保管她乖乖跟你走。”老王头对村长谄笑。柴房外,招娣举起火把:“书给我,不然烧了马家屋子。”月光照亮老王头猥琐......
第10章








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