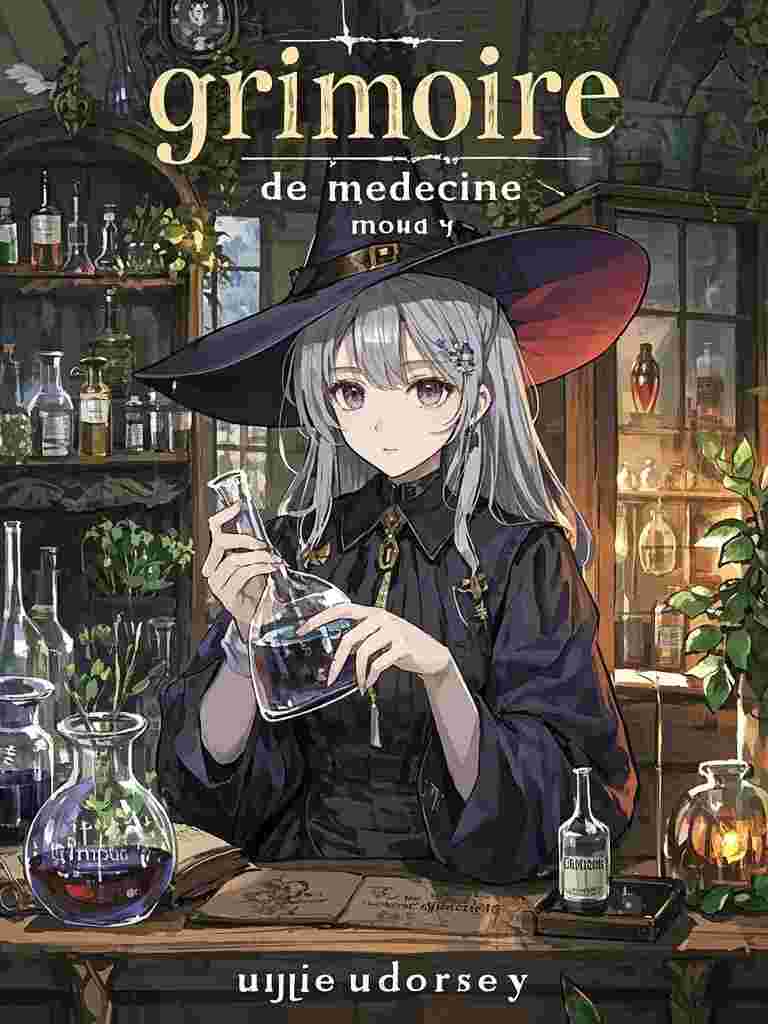将阿水那张没什么表情的脸映得忽明忽暗。
她看着闻潮生从怀里掏出那把柴刀——刀身雪亮,薄得惊人,在火光下流转着冰冷致命的寒芒。
他找了一块还算平整的石头,又从角落里翻出一个用破布包着的小东西,打开,是一块边缘粗糙、沾满污渍的磨刀石。
水,是外面刚取的雪水,盛在豁口的破碗里,冰冷刺骨。
滋啦——滋啦——磨刀石粗糙的表面刮擦过薄薄的刀刃,发出单调而刺耳的声响,在寂静的破庙里被无限放大,压过了风雪的呜咽。
闻潮生抿着唇,眼神专注得可怕,每一次推拉都带着一种近乎虔诚的狠绝。
水珠顺着刀身滑落,滴落在冰冷的泥地上,晕开一小片深色的湿痕。
阿水抱着膝盖,坐在火堆对面,目光没有离开闻潮生磨刀的手。
火光在她眼底跳跃,却照不进深处那片沉寂的幽潭。
“刀磨得太薄了,”她忽然开口,声音没什么起伏,却像一块石头砸破了压抑的寂静,“容易崩口。”
闻潮生磨刀的动作没有丝毫停顿,甚至没有抬头,只是从喉咙深处滚出一声低沉的回应:“嗯。”
“杀人,和杀蛙不一样。”
阿水继续说,语气平淡得像在讨论天气,“蛙不会躲,不会喊,不会用临死前的眼神看你。
人,会。”
滋啦——滋啦——磨刀声持续着,节奏稳定得令人心头发慌。
闻潮生终于抬起眼皮,看了阿水一眼。
火光下,他眼底的血丝清晰可见,像盘踞的毒蛇。
“那又如何?”
他声音嘶哑,“我的命,早就不值钱了。
换他一条命,值!”
阿水沉默了片刻,似乎在斟酌词句。
她挪了挪身子,离火堆更近了些,伸出枯瘦的手烤着火。
“杀了他,然后呢?”
她问,目光终于从刀上移开,落在闻潮生脸上,“你死了,或者亡命天涯。
苦海县换一个县令,流民沟还是流民沟,埋骨坡照样埋人。
刘金时死了,这世道就能变好吗?
你闻潮生,就能活成人了?”
她的声音不高,却像淬了冰的针,精准地扎进闻潮生沸腾的恨意里最深处那点虚妄的幻想。
闻潮生磨刀的动作猛地一顿!
粗糙的磨刀石边缘狠狠刮过他的拇指指腹,瞬间划开一道口子,鲜血涌了出来,滴落在雪亮的刀身上,迅速晕开、凝固,变

天不应闻潮生阿水全局
推荐指数:10分
《天不应闻潮生阿水全局》这本书大家都在找,其实这是一本给力小说,小说的主人公是闻潮生阿水,讲述了风雪像刀子一样刮过闻潮生的脸。他裹紧身上那件辨不出颜色的破袄,深一脚浅一脚地跋涉在齐膝的雪里。怀里的鹿皮小包硌着肋骨,里面裹着的三只冻僵青蛙是他和破庙里那个不速之客今晚的口粮。三天前,他就是在这片被苦海县百姓称作“埋骨坡”的雪原上,刨出了半截身子冻成青紫色的阿水。当时,她的一只手倔强地伸出雪堆,像一......
第7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