印记。
那根为祸一切的“借寿烛”,连同那神秘冰冷的铁皮盒子,早已在剧烈燃烧和撞击中化为几点零星的残渣,无声无息地混入了冰冷污秽的泥土里。
一阵风打着旋掠过,带起几片枯叶和灰尘,将它们彻底掩盖。
不知道过了多久,肆虐了一夜的风终于小了些,只剩下零星的冰冷雪沫子从灰暗的天空飘落。
乱葬岗被一层薄薄的灰白覆盖,如同死人盖上的尸布。
破败的枯树、塌陷的坟包,一切都显得僵硬而死寂。
唯有几道歪斜杂乱的新脚印和几点冻成冰坨的暗红、乌黑血迹,证明昨夜并非梦境。
四具形态各异的尸骸静静地躺在同一个方向的寒泥之中,构成一幅诡异死寂的图卷:一具形销骨立,背靠焦黑槐树;一具枯干如柴,裹着华贵绸缎;一具蜷缩扭曲,焦炭冒烟;还有一只冻硬的野狗尸体。
不远处,只有一个破旧的、盖子摔掉了的锡皮盒子,空空荡荡地躺在一片被踩踏凌乱的烂泥坑里,粘着泥点、沾染了些许干涸的污黑血迹,反射着一点天光,显得冰冷而讽刺。
村头柳家那间破旧的茅草屋里,气息似乎真的被抽走了所有衰朽。
柳氏奇迹般地下了炕,虽然腰背佝偻得更厉害,但那些索命的咳嗽竟像一阵风刮过般,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脸色虽然依旧苍白,却透着一丝久病初愈后的红晕,仿佛枯木逢春。
她摸索着在灶间熬了一小锅稀薄的粟米粥,双手捧着碗,小口小口地喝着。
动作很慢,却很稳。
门外邻居张大娘探头进来:“柳婶子…咳…好些了?”
柳氏抬起头,咧了咧干瘪的嘴角,想挤出一个笑,但那弧度僵硬得像用刀刻上去,眼睛直勾勾地望着门外那条空荡荡的小路:“好…好些了…可俺三儿…咋还不回?”
张大娘张了张嘴,喉咙里像堵了团棉花,最终还是重重叹了口气,摇摇头快步走了。
晌午时分,几个本家的远房叔伯辈,脸色凝重,用半扇破门板抬了点物件回来——那是柳三仅有的几件旧衫和一双破鞋。
他们在村外那片向阳的野坡上,刨了个浅浅的土坑,草草埋了。
算是衣冠冢。
柳氏被搀扶着到了那小小的新土包前。
她没有像众人预想那样哭天抢地,只是呆呆地站着,灰白的头发在北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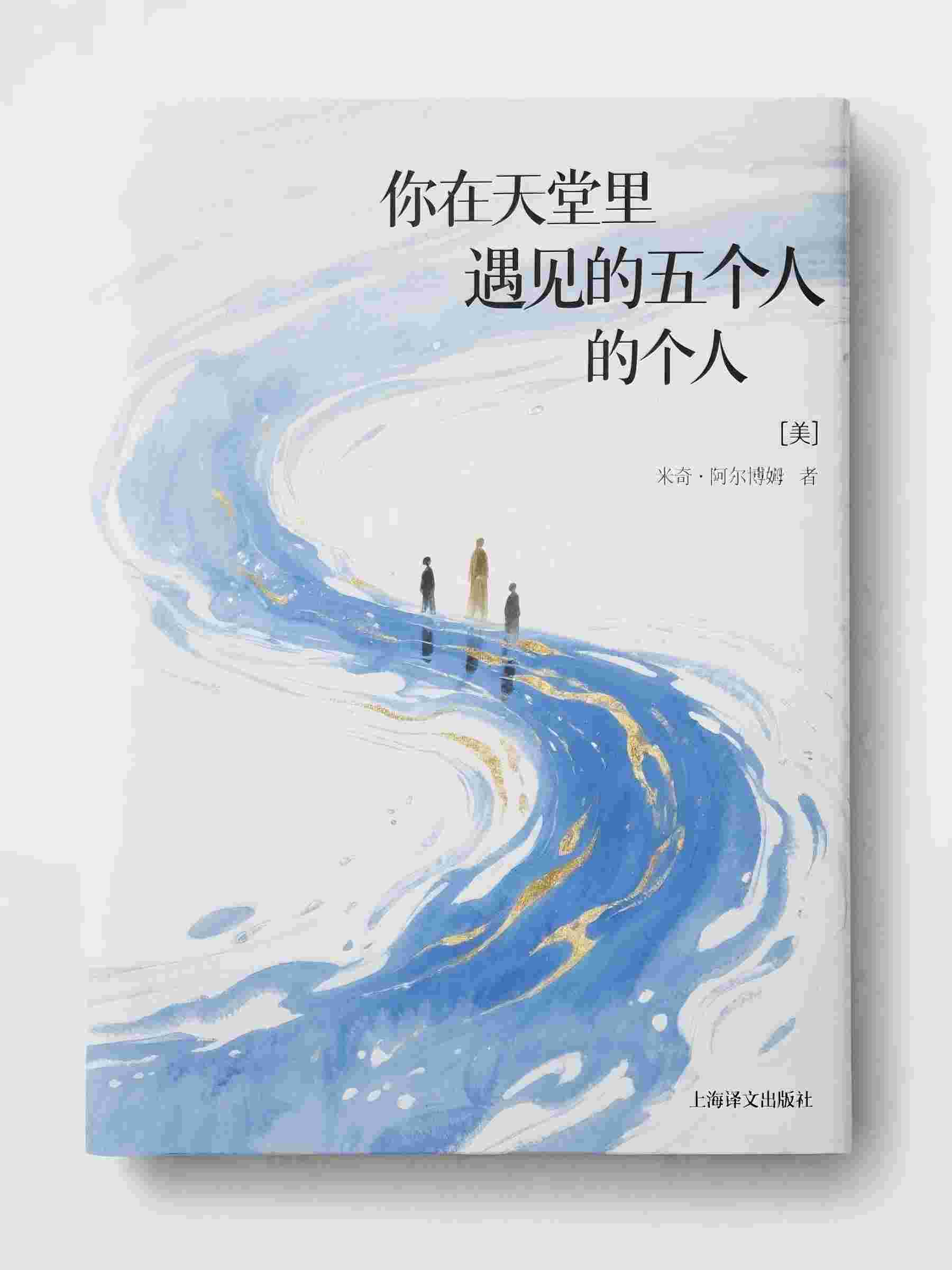
借寿烛,烧一刻,少活十年!后续+完结
推荐指数:10分
主角是柳三回春堂的现代言情《借寿烛,烧一刻,少活十年!后续+完结》,是近期深得读者青睐的一篇现代言情,作者“乾关北侯”所著,主要讲述的是:嘉靖年间灾荒连年,我娘病得快断了气。回春堂坐堂大夫眼皮都不抬:“玉屏散三钱银子一副,先抓五副。”我在破庙神像下摸到个铁皮盒,里面是根暗红如血的蜡烛。老更夫临死前的话在耳边炸响:“沾着血光寿数……碰不得!”可当我看见母亲咳出的黑血浸透了破褥子时,还是颤抖着点燃了它。烛火窜起的瞬间,脑子里响起个冰冷声音......
第13章








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