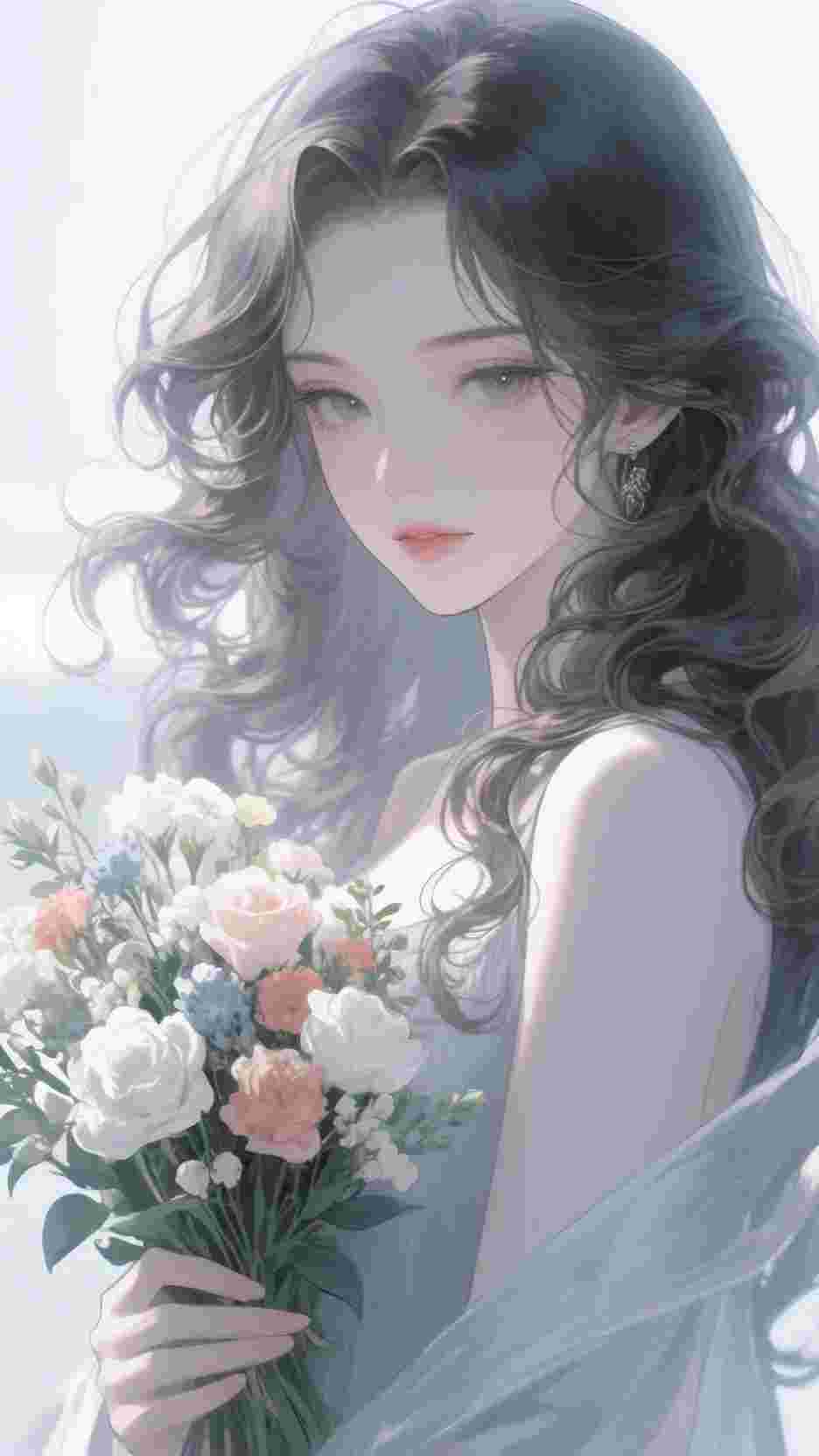事?”
他的语气,带着一丝不悦。
“我弟弟……他快不行了!”
我语无伦次,抓着他的胳膊,像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,“他需要钱,需要五百万做手术!
藏舟,求你,你帮帮我!”
他听完,脸上的表情,没有丝毫变化。
他只是,一根根地,掰开了我紧抓着他的手指。
“冷静点,苏烬。”
“我很冷静!”
我哭喊道,“我只要五百万!
你可以卖掉一幅画!
就那副……那副德加的《舞女》,上次佳士得的估价,就超过了一千万!
只要卖掉它,我弟弟就有救了!”
“不行。”
他想都没想,就拒绝了。
“为什么?”
我难以置信地看着他。
“那幅《舞女》,我准备将它纳入明年的艺术品信托基金计划里。
现在卖掉,会打乱我所有的部署。”
他看着我,眼神冷得像在看一个无理取闹的陌生人,“苏烬,你要分清主次。
任何藏品,没到最佳的抛售时机,都不能动。”
他顿了顿,说出了一句,将我彻底打入地狱的话。
“包括你。”
包括你。
原来,在他眼里,我和那些画,真的没有任何区别。
都是他的藏品,都需要在他设定的、最佳的时机,才能发挥价值。
我的弟弟,一条活生生的人命,在他的商业部署面前,一文不值。
“傅藏舟……”我的声音,因为绝望而嘶哑,“那是一条人命啊……苏烬,”他看着我,眼神里甚至带上了一丝怜悯,那种对无知者的怜悯,“你要学会接受现实。
艺术,是永恒的。
而人,不是。”
艺术是永恒的,而人,不是。
好。
好一个,艺术是永恒的。
我看着他,看着这张我曾痴迷过的、英俊的脸,突然笑了。
我笑得眼泪都流了出来。
我不再求他,不再哭喊。
我只是,平静地,站直了身体,然后,转身,离开了书房。
我知道,我心里,有什么东西,在那一刻,彻底地,枯萎了,死去了。
回到房间,我做了一件事。
我给我那个在业内德高望重的前辈,打了一个电话。
“王老师,您上次说,中东那位萨勒曼王子,一直在打听梵高《加歇医生肖像》的下落,对吗?”
“是啊,小烬,怎么了?”
“您帮我联系他。”
我的声音,平静得可怕,“告诉他,三个月后,让他来中国。
我会给他一个

焚画那天他下跪加歇傅藏舟番外
推荐指数:10分
小说叫做《焚画那天他下跪加歇傅藏舟番外》是“雨神写书”的小说。内容精选:火。烈焰的腥甜气息,混合着松节油和百年画布燃烧的独特香气,像一只无形的手,扼住我的咽喉。我赤着脚,站在私人美术馆冰冷的大理石地板上,手里握着一枚滚烫的Zippo打火机。我的面前,是文森特·梵高的《加歇医生肖像》。市场估值,十亿人民币。这是傅藏舟的骄傲,是他庞大艺术品帝国皇冠上的主钻石。现在,这颗钻石......
第7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