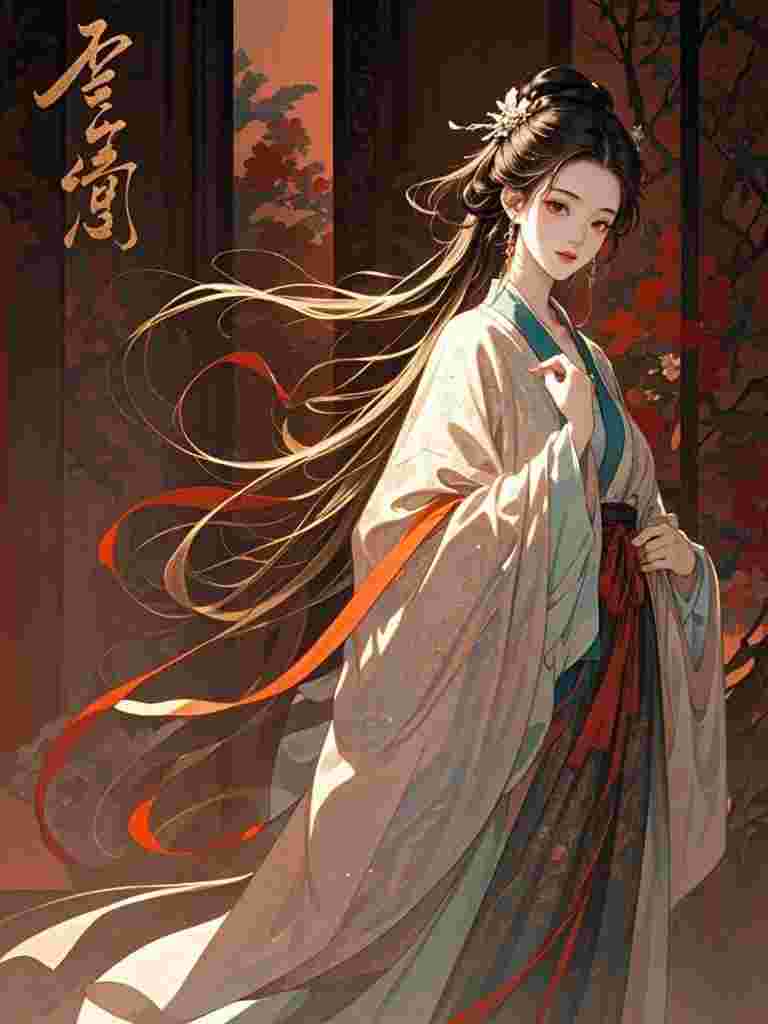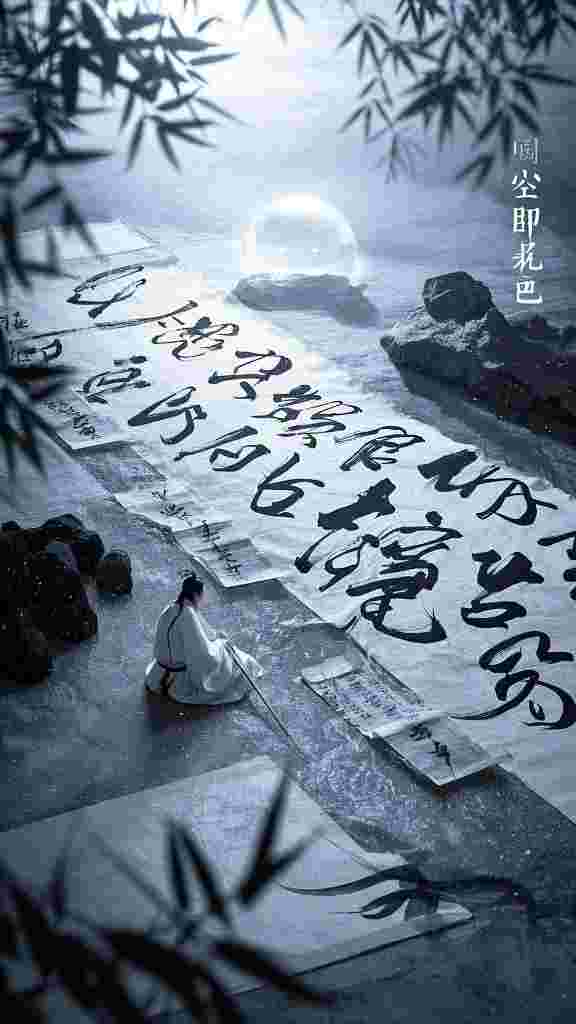碰到一起,分享彼此的喜悦与忧愁。
而不是像藤蔓一样,必须依附于另一棵树才能存活。
所以,我沉浸在我的古籍世界里。
我发表了几篇在极小领域内颇受好评的学术论文,成了几个权威专家口中“颇有前途的年轻人”。
我修复了一本几近损毁的宋代孤本,那份成就感,远比银行账户里多几个零要来得真实。
我以为,我正在变成一棵更好的树。
我以为,我做好了迎接春天的一切准备。
我只是忘了,树是不能移动的。
如果风停了,那两棵树,即便离得再近,也永远无法触碰。
等待的第七年,秋天。
我收到了陈汐的一封信,而不是一张明信片。
这七年来,这是第一次。
信封是牛皮纸的,很厚,上面贴着来自阿根廷的邮票。
邮戳的日期是一个月前。
我的手在颤抖。
我花了整整十分钟,才用裁纸刀小心翼翼地划开信封,生怕弄坏了里面任何一点可能的内容。
信纸很长,足足有五页。
她的字迹还和以前一样,带着一种急切的、不耐烦的美感。
信里,她没有说太多关于风景的话。
她第一次,详细地描述了她的疲惫。
她说她厌倦了永远在路上的感觉,厌倦了在陌生城市里醒来时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的恐慌,厌倦了镜头里永远是别人的生活而没有自己的。
她说,她想家了。
信的最后,她写道:“阿舟,我准备回去了。
也许是最后一次回去了。
两个月后,十一月。
等我。
这次,换我来跑大半个城市,去见你。”
那一刻,我感觉我生命里的整个寒冬,都在这句话里被撞得粉碎。
积压了七年的冰雪,瞬间融化,汇成一股暖流,冲刷着我几乎已经麻木的四肢百骸。
我坐在窗前,看着窗外开始飘落的樟树叶,第一次觉得,原来秋天也可以是春天的序曲。
路灯,好像真的要一盏一盏亮起来了。
我要亲眼去看看,那个我等了七年的春天,到底是怎么样赢的。
我开始像一个即将迎接新婚的新娘一样,笨拙而狂热地准备着。
我把那个小小的、只属于我一个人的公寓,翻来覆去地打扫了无数遍,直到地板光亮得能映出我的影子。
我买了很多新的东西,新的床单,新的窗帘,新的拖鞋——一双男士的,一双女士的。
我甚至开始

你也一定走了很远的路吧抖音热门结局+番外
推荐指数:10分
《你也一定走了很远的路吧抖音热门结局+番外》是作者 “我也不曾來過”的倾心著作,抖音热门是小说中的主角,内容概括:我叫林舟。舟,一叶扁舟的舟。父母为我取这个名字时,或许是希望我能像水上的小船一样,随波逐行,自在安逸。他们显然失算了。我成了一艘没有桨、没有帆,却在港湾里自行凿穿了船底的破船,心甘情愿地沉溺在名为“过去”的死水里。我的职业是古籍修复师。更准确地说,是这座城市最古老大学图书馆特藏部里,一个比那些藏品还......
第5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