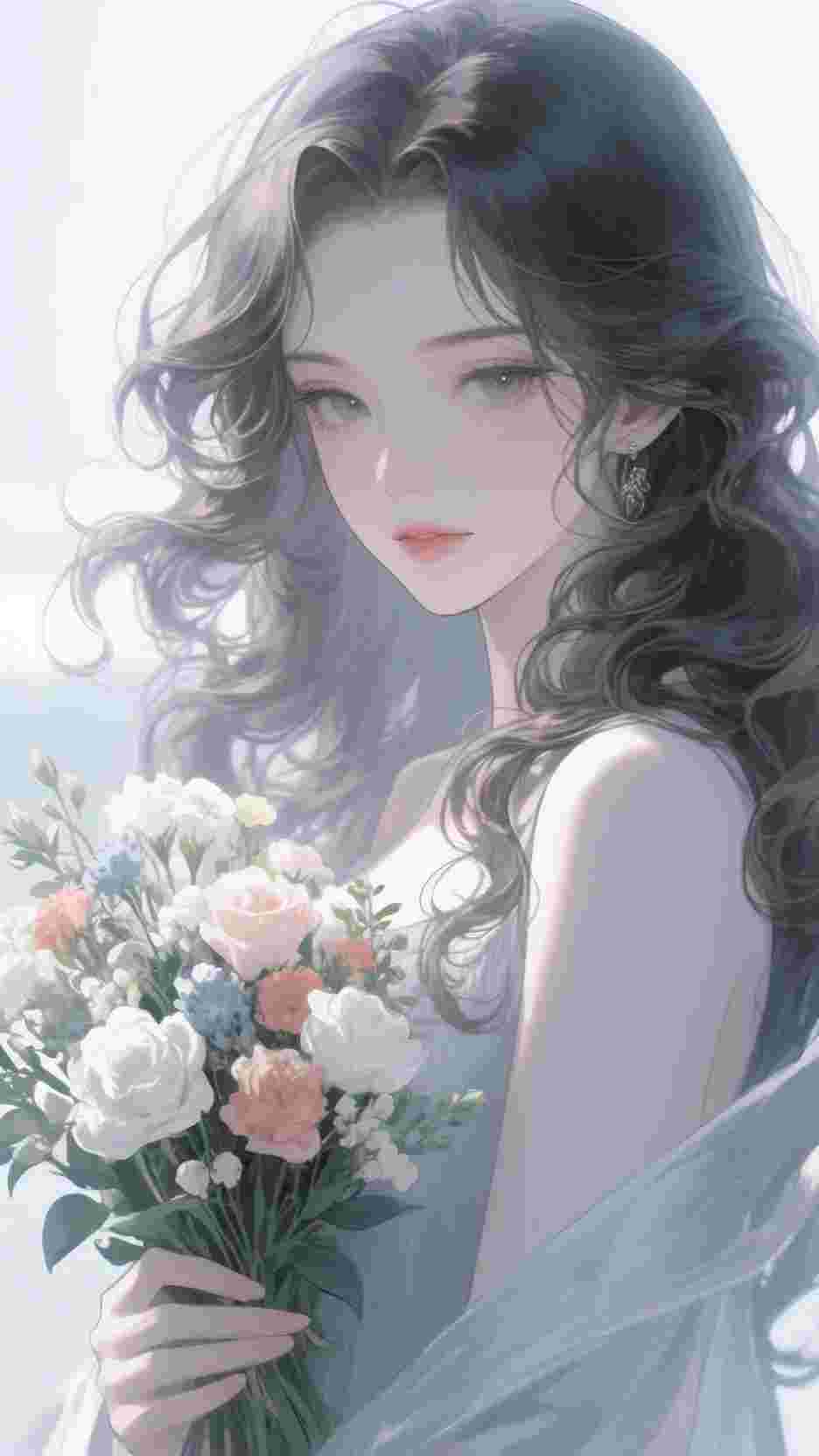,“装什么清高?
舍不得富贵就直说。
你跪下来磕三个响头,我替你求母亲留你做丫鬟,如何?”
前世,我就是在这样的羞辱下崩溃的。
此刻,我只抽回胳膊,从袖袋摸出一个荷包。
褪色的宝蓝缎面,绣着歪扭的梅花——我七岁时学女红的第一个成品,母亲曾当宝贝收着。
“姐姐说笑了。”
我将荷包塞进她掌心,“你的东西,我还你。”
宋玉瑶像被烙铁烫了手,猛地甩开!
荷包掉在地上,滚出一枚小小的梅花玉扣。
<“谁要你的破烂!”
她尖声后退,仿佛沾了瘟疫。
母亲冲过来,一巴掌扇在我脸上!
“下贱胚子!”
她气得浑身乱颤,“滚!
带着你的腌臜爹娘滚!
这辈子别脏了侯府的门!”
火辣辣的疼在颊边蔓延。
我弯腰,捡起玉扣和荷包。
玉扣冰凉,是那年我发烧,母亲整夜抱着我,汗水浸断了她的玉扣链子,我醒来后哭着给她补的。
“夫人保重。”
我将玉扣放在高几上,挨着那对木镯,“晚宁告辞。”
再没看任何人,我一手扶起云大河,一手搀住柳氏,转身朝厅外走。
寒风卷着雪沫扑进廊下。
柳氏把怀里紧抱的蓝布包袱抖开,是一件半新的厚棉袄,絮得鼓鼓囊囊。
“快、快穿上……”她手忙脚乱地往我身上裹,“冻坏了……”棉袄带着陈年的皂角味和阳光的气息。
我系好布纽,听见身后传来宋玉瑶娇脆的嗤笑:“烂泥里的草籽,真当自己能开出凤凰花?”
云家在京郊大柳树村,三间土坯房,篱笆院。
柳氏一进门就忙着烧炕,云大河闷头劈柴,灶膛的火光映着他沟壑纵横的脸。
前世我病着被拉回来,头三天水米不进,只缩在炕角哭。
柳氏把家里唯一的母鸡杀了煨汤,我嫌腥气,一把掀翻了碗。
如今,我端起粗陶碗。
粥是糙米混着野菜,热腾腾地烫嘴。
“慢点,慢点吃……”柳氏搓着手,小心翼翼觑我脸色。
“娘,”我咽下粗糙的粥粒,“咱家还有多少粮?”
云大河闷声道:“撑到开春……难。”
柳氏眼眶红了:“都怪我们没本事……开春就好了。”
我放下碗,“爹,咱家后山朝阳那坡地,是不是荒着?”
前世,我饿死在永昌十六年的春天。
死前最后一口是观音土。
那

朱门假千金,寒门真凤凰!(番外)+(全文)
推荐指数:10分
小说《朱门假千金,寒门真凤凰!(番外)+(全文)》,相信已经有无数读者入坑了,此文中的代表人物分别是宋玉瑶寒门云,文章原创作者为“景三Yying”,故事无广告版讲述了:我是宋家养了十五年的假千金。真千金归府那日,全家嫌恶地要我滚出侯府。前世我跪着哀求,却被真千金推进冰湖活活冻死。这一世,我主动向寒门云家走去:“爹,娘,我跟你们回家。”真千金笑我蠢:“荣华富贵不要,偏去啃烂泥?”后来,我种出的胭脂米成了御贡,寒门哥哥高中状元。而真千金为攀高枝,在侯府饮下绝子药。她发......
第4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