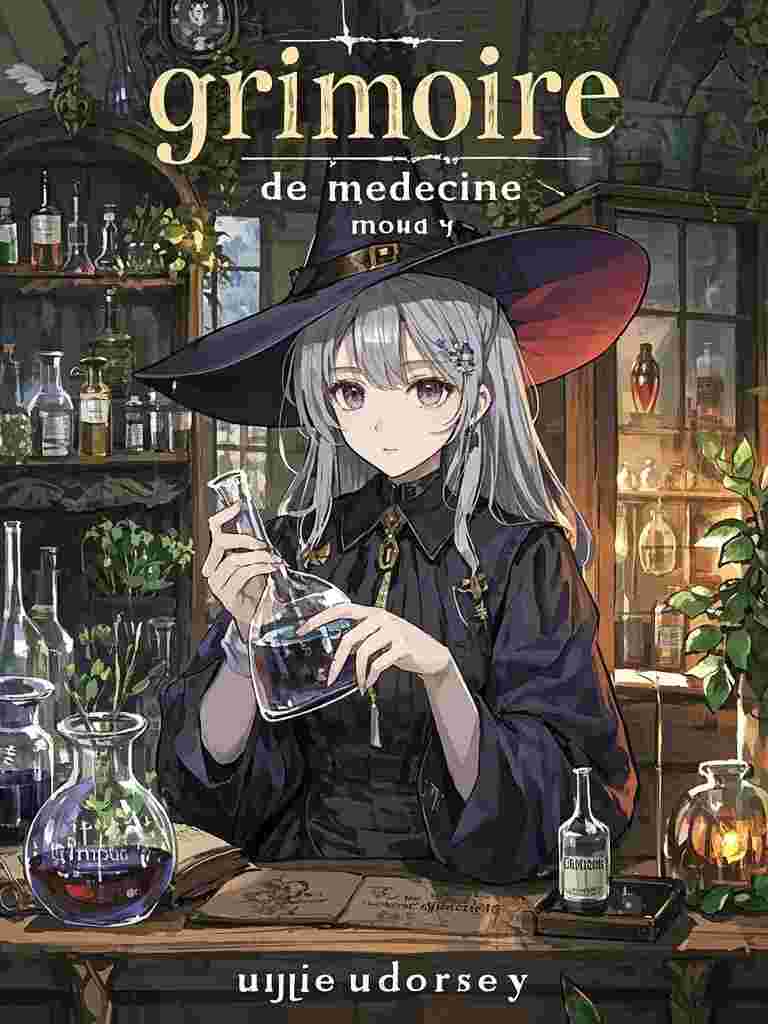响之后,心里那股几乎要爆炸的窒闷,似乎被强行凿开了一道缝隙。
冰冷的空气灌了进来,带着机油和铁锈的味道。
我慢慢松开扳手,任由它“哐当”一声掉落在冰冷的水泥地上。
声音在死寂的店里回荡。
回荡的声音同时也在我心里不停的响起,我告诫自己,我该醒醒,我不能这样。
“尺寸不对的缸头垫片,自己去库房找。”
我背对着他们,声音恢复了之前的沙哑,却带上了一种奇异的、近乎虚脱的平静,“找不到,今天就别下班了。”
我走到角落的水池边,拧开锈迹斑斑的水龙头。
冰冷刺骨的自来水哗哗冲下,浇在沾满黑黄油污的手上。
我用力搓洗着,指甲刮过皮肤,留下道道红痕。
水珠溅到脸上,顺着下巴滴落,分不清是水还是别的什么。
镜子模糊的倒影里,只看到一张沾着水渍和油污的、苍白而陌生的脸,眼神空洞得像两口枯井。
时间像个冷酷的推手,不管不顾地把人推向那个注定到来的节点。
28号。
周六。
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出了门,又是怎么样,打扮成这样来到了这儿,也真是太怂了。
天气好得近乎残忍。
天空是那种毫无杂质的、水洗过般的湛蓝,阳光毫无遮拦地倾泻而下,照得凯悦酒店巨大的玻璃幕墙闪闪发光,晃得人睁不开眼。
酒店门口巨大的充气拱门上,贴着硕大的金色双喜字,在阳光下反射着刺目的光。
空气中弥漫着甜腻的花香和喜庆的音乐声,穿着光鲜的宾客们脸上洋溢着笑容,三三两两,谈笑风生地步入那扇旋转的、仿佛通往另一个世界的玻璃门。
隔着一条车水马龙的宽阔街道,我靠在人行道一棵法国梧桐粗糙的树干上。
引擎的余温透过厚重的皮衣布料,熨贴着我冰冷紧绷的后背。
身下的“暗影”,我那辆改装过的黑色川崎Vulcan S,像一头蛰伏的巨兽,沉默地吞吐着尚未散尽的汽油味。
巨大的V型双缸引擎在怠速下发出低沉而规律的脉动,如同我胸腔里那颗沉重跳动的心脏。
我深吸了一口气。
空气里浮动的花香和隐约的婚礼进行曲旋律,混合着尾气的味道,钻进鼻腔,带着一种令人眩晕的甜腻。
手指有些僵硬地扣上那顶哑光黑色的全盔面罩。
视野

我们就该错过后续+完结
推荐指数:10分
无删减版本的现代言情《我们就该错过后续+完结》,成功收获了一大批的读者们关注,故事的原创作者叫做无疆,非常的具有实力,主角陈屿林晚。简要概述:我和陈屿熬过七年异地,却败在他母亲一句“单亲家庭的孩子心理不健全”。而他却不得不放手他婚礼那天阳光刺眼,我裹紧黑色大衣混在宾客中。台上他笑得开怀,三次目光扫过人群,却始终没认出帽檐下的我。南方的暮春,空气里总裹着一种湿漉漉的沉,像吸饱了水的棉絮,闷得人喘不过气。窗外的樟树叶子油绿得发亮,水珠沿着叶尖......
第6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