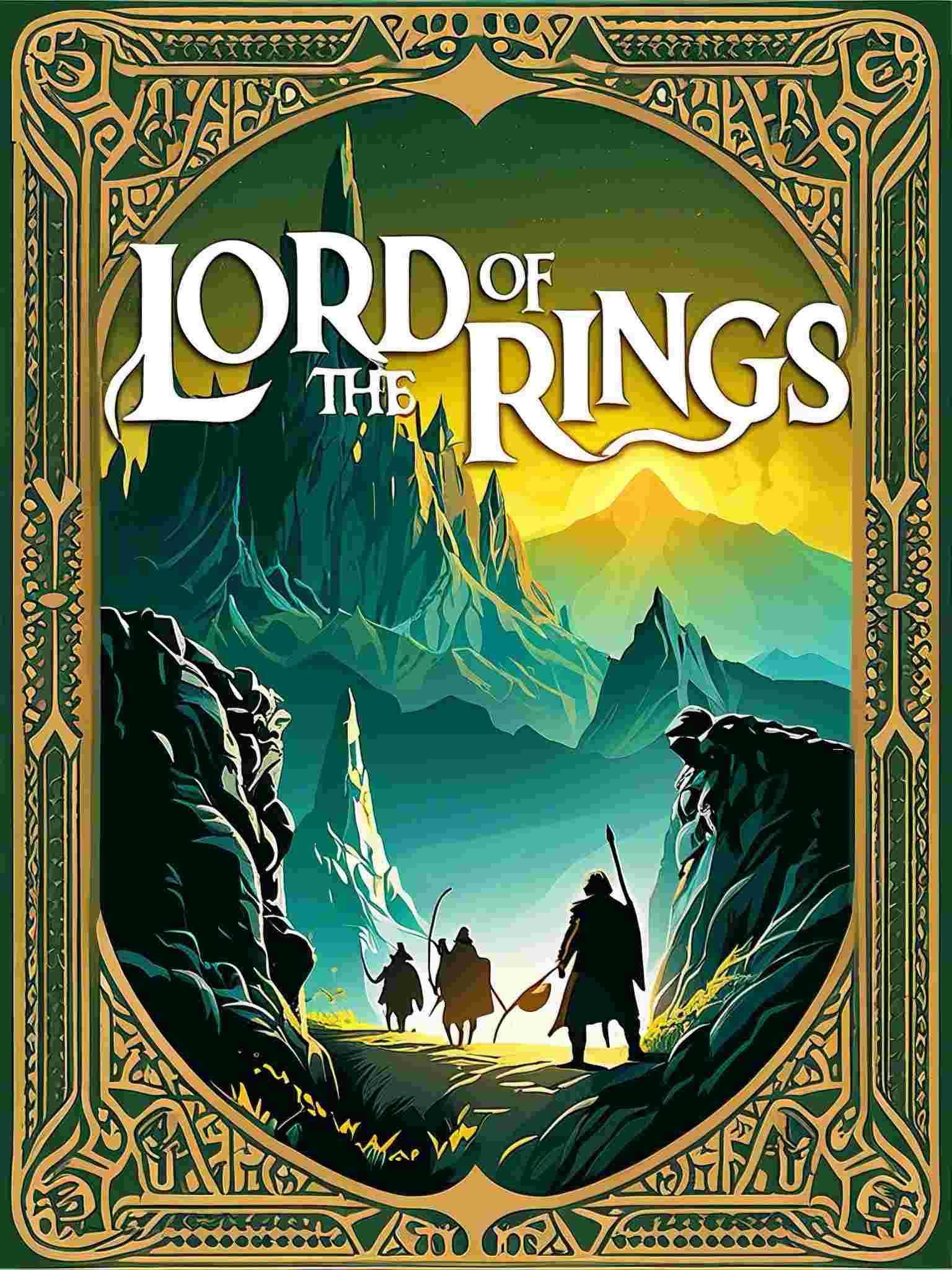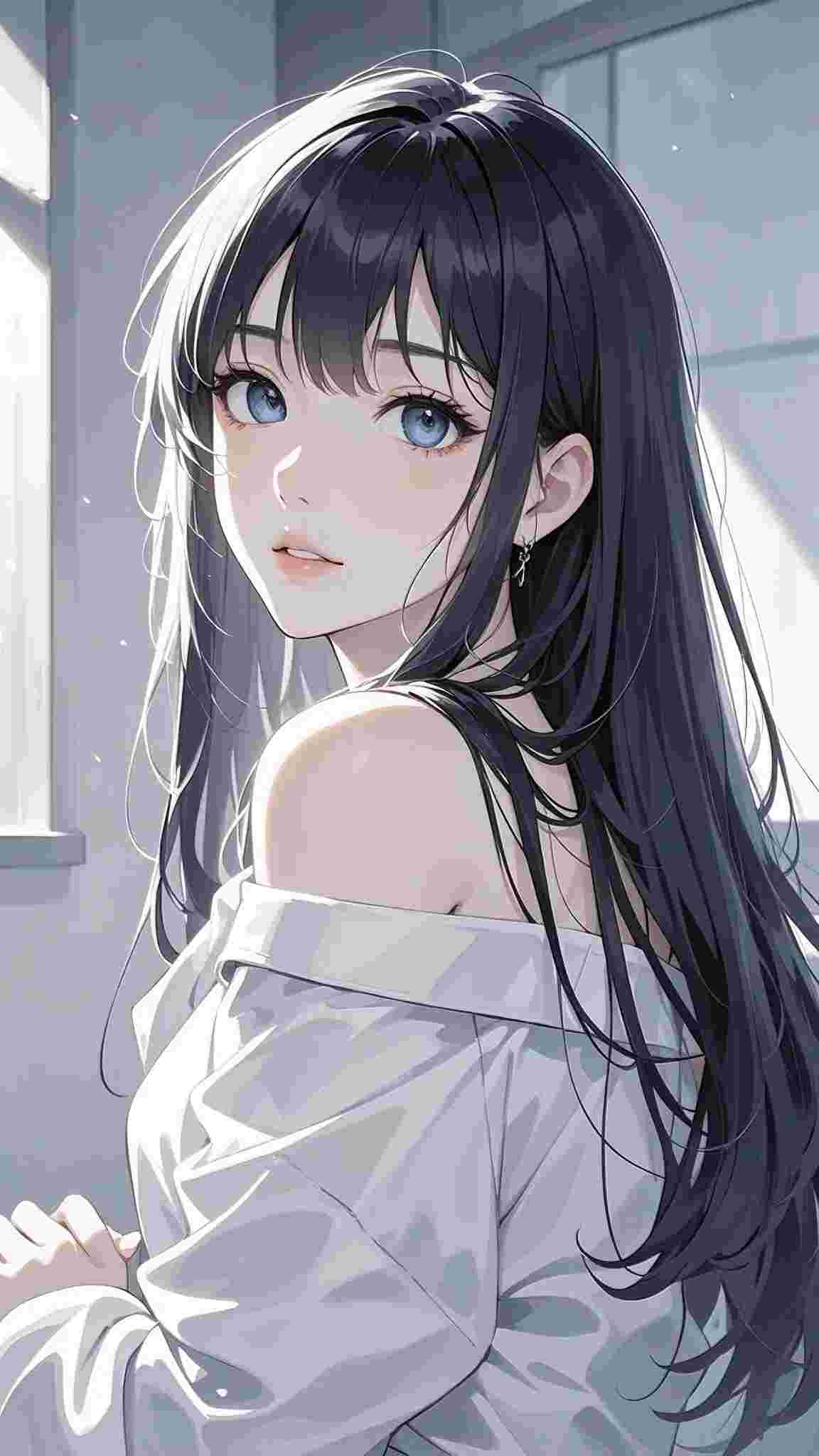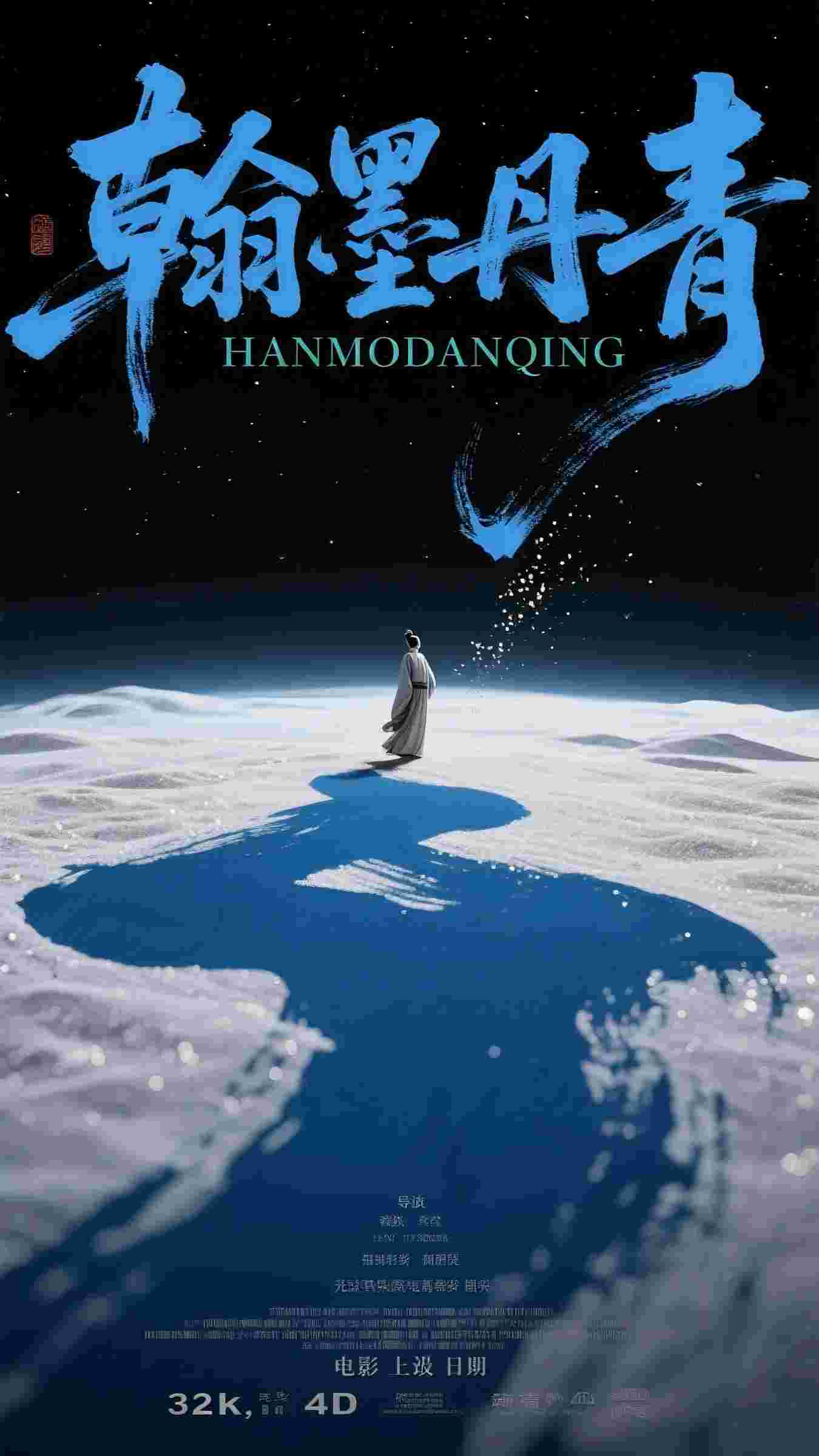音保养得极好,却淬着毒,“暮歌像你这么大的时候,活泼得像只百灵鸟。
血型一样,怎么人就天差地别?
真是烂泥扶不上墙。”
林知意垂着眼,盯着面前那只污秽的狗食盆,指甲深深掐进掌心,留下几个月牙形的白痕。
痛感让她维持清醒。
周婉似乎也没期待她的回应,更像是在对空气宣读她的罪状:“记住,你活着唯一的价值,就是你这身血,这幅健康的身子骨。
安分守己,到时候乖乖把该给的给了,林家还能赏你一口饭吃。
别动那些不该有的心思,晦气。”
高跟鞋声哒哒远去,融进那片繁华的喧嚣里。
夜深了,宴会厅的灯火渐次熄灭。
别墅巨大的轮廓沉入黑暗,像一头蛰伏的巨兽。
廊下的感应灯灭了,只有远处庭院地灯投来一点微弱的光。
林知意从旧棉絮里摸索出一小块被油纸包裹的东西。
是厨房那个总低着头、不敢看她的帮佣小姑娘,趁老陈不注意,偷偷塞给她的。
一块干硬的黄油面包,已经有些掉渣了。
她小口小口地啃着,用唾液慢慢软化,不敢发出太大声音。
每一口下咽,都像用砂纸摩擦过喉咙。
这点微不足道的能量,是她活下去的燃料,更是复仇的火种。
油纸底下,还藏着一小块边缘锐利的碎玻璃,是她几天前故意打碎一个废弃花盆藏起来的。
她用冰凉的指尖反复摩挲着那片玻璃的尖角,轻微的刺痛感让她混沌的头脑变得异常清晰。
明天。
她在心里一遍遍勾勒那个画面。
明天,属于林暮歌的盛大纪念日,她会送上一份让所有人心惊肉跳的“贺礼”。
翌日傍晚,林家别墅前所未有地喧闹起来。
政商名流、媒体记者,衣香鬓影,觥筹交错。
巨大的水晶吊灯将厅内照得恍如白昼,空气中弥漫着昂贵香槟和香水的气息。
林知意被打扮了一番。
头发梳得光滑,脸上扑了厚厚的粉,试图掩盖长期营养不良的憔悴和蜡黄。
她身上那件淡粉色的纱裙,是林暮歌生前最喜欢的款式和颜色,穿在她过于清瘦的身上,空荡荡的,像个偷穿了大人衣服、拙劣模仿的小丑。
她被安排在宴会厅最不起眼的角落,像个展览品,又像个随时待命的移动血库。
无人与她交谈,那些投来的目光要么是轻蔑的审视

金丝雀反杀训鸟人林暮歌林国栋:番外+无删减版
推荐指数:10分
热门小说《金丝雀反杀训鸟人林暮歌林国栋:番外+无删减版》近期在网络上掀起一阵追捧热潮,很多网友沉浸在主人公林暮歌林国栋演绎的精彩剧情中,作者是享誉全网的大神“武云天”,喜欢现代言情文的网友闭眼入:>被豪门收养那天,我就知道自己是白月光的器官容器。>他们冷眼看我啃馊饭、睡狗窝,只为保持与她相同的稀有血型。>十八岁生日宴上,我故意摔碎她生前最爱的古董花瓶。>养父掐住我脖子时,我笑着打开直播手机:“恭喜林先生,谋杀亲女冲上热搜第一。”>警笛声中,我擦着嘴角血渍走向遗产公证处。>原来他们不知道,那女......
第2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