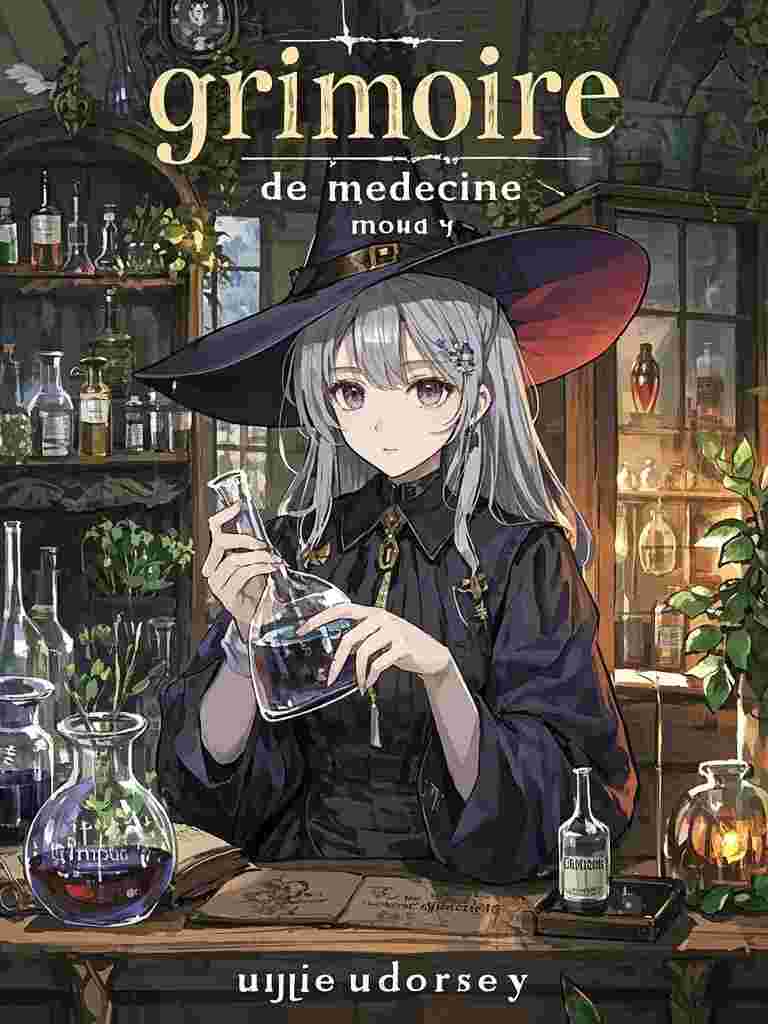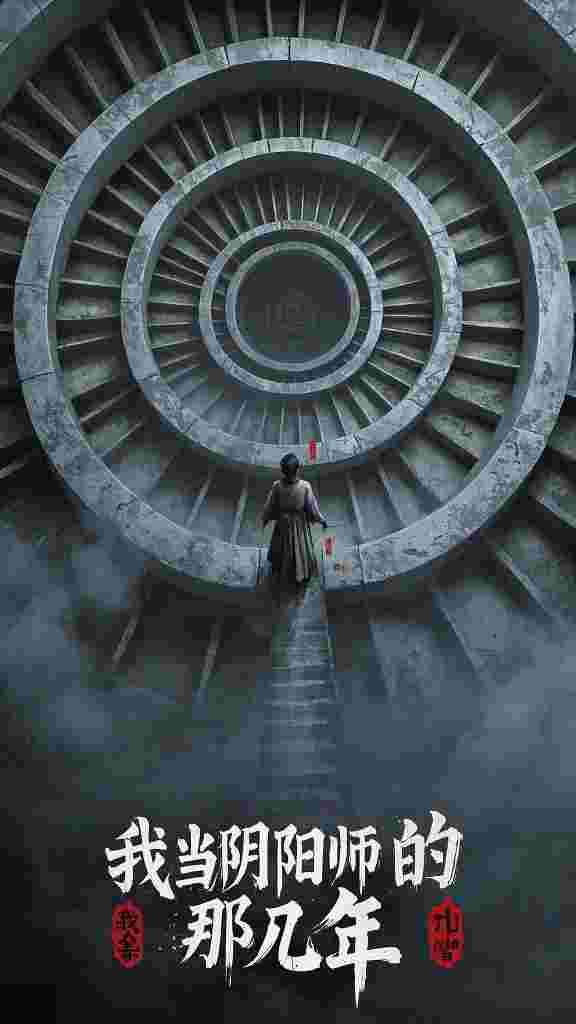行、望、听”。
每组写四句,每句不超过十个字。
她让他们“不必用比喻,先把你们‘看见’的东西写下来”。
学弟学妹们一开始拘谨,慢慢打开,写出好几句生的、却动人的句子。
比如:“醒:风把我的肩叫醒。”
比如:“望:窗外的树在看我。”
她把这几句收下,写在大白纸上,贴到展板旁边:“读者注脚”。
读者的词也可以被看见。
中午,她和顾行把温室的“靠写”送去许师傅那里做终版。
许师傅神色认真,把每一张都在斜光下看了一遍,点头:“这批好了。”
他把一张纤维基的“靠”递给林澄,“你摸摸这个边——纸有温度。”
“纸有温度。”
她重复了一遍,像遇见了一个美而准确的说法,“谢谢您,师傅。”
“用好它。”
许师傅咧嘴笑,“让看的人摸到你们的认真。”
周一,风起得比前几天更早。
她在课间合上本子,给自己写了一句:“注11:明天,带一件颜色浅一点的衣服。”
她想在病房里轻一些,像一块不太占地方的白。
她不打算告诉母亲——她知道若现在说,母亲会千里迢迢坐车赶来,而她并不想把“未知”变成家里一件沉甸甸的盆,她想先把它用文字晾干,再带回去给家里看。
周二清晨,天空是一个被水洗过的浅蓝。
她提前半小时到医院。
挂号、取号、排队,走廊的椅子一排排,像被剪齐的草。
护士把她带进检查室,关灯,机器的冷光在黑里显得孤独。
她把下巴放到托上,尽量让眼睛不乱动。
医生说:“看红点。”
她看。
红点一会儿在右,一会儿在左,像一只灵巧的虫。
她听到机器“滴”的一声,又“滴”的一声——她知道那是机器在记录她的“看”。
检查结束,医生说了几句,“看起来稳定。
夜间可能会更敏感一些,不要在强光下久看。
一个月后复查。”
医生说话的语速很平,一点也不吓人。
她点头,把这些词一一写在心里,然后在心里用铅笔轻轻划了几下,把它们从“威胁”削到了“建议”。
她走出检查室,把口罩摘下来透了一口气,给顾行发了一条短信:“多云转晴,风不大。”
两分钟后,她的手机亮了一下——一张图发过来,是图书馆台阶上的两个

花期将尽3顾行林澄全文+番茄
推荐指数:10分
小说叫做《花期将尽3顾行林澄全文+番茄》,是作者“思念舞伶雪”写的小说,主角是顾行林澄。本书精彩片段:第四章、十词十景的第一束光傍晚六点一刻,操场的红还在太阳底下微微发烫。风从湖上绕过理科楼的转角,进了看台下的空腔,吹出一声细长的呜。跑道内圈有两队新生在练短跑,口号拉得很高,落在地面的时候却被风削圆了边,听上去像一串在嘴里慢慢化开的糖。顾行把相机的肩带斜斜挂好,另肩背着一个浅灰的帆布袋,里面是备用电......
第7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