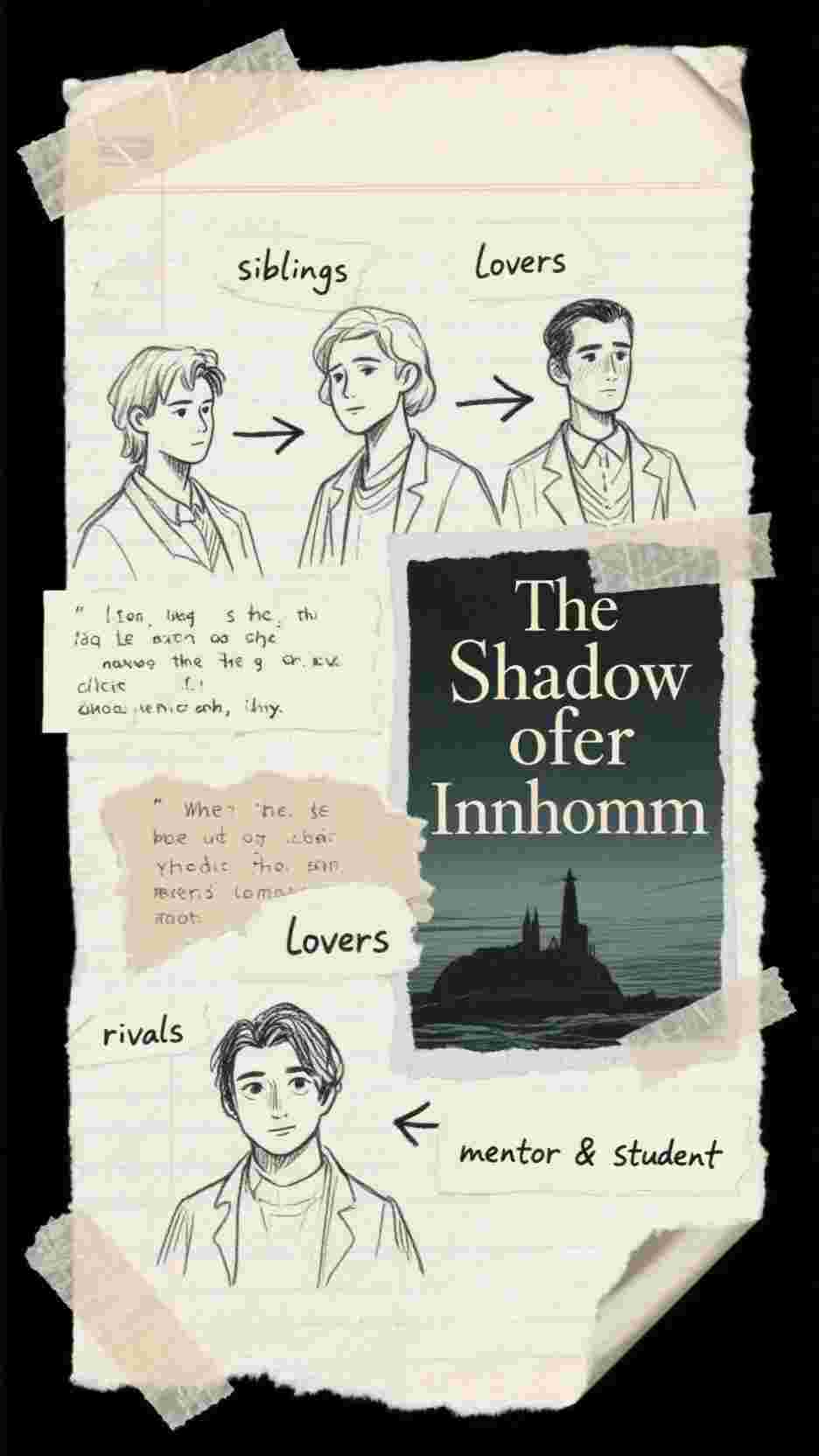着淡绿色的、带有轻微腐蚀性和神经毒性的雾气。
迷宫有两条主要路径,每隔一段时间会随机切换安全的那一条。
游戏规则变了:蝼蚁需要在一炷香的时间内,穿过迷宫,找到出口。
而作为庄家,我必须在每次游戏开始前,亲自进入迷宫,用自己的身体“校准”路线——安全路径上设有特殊的感觉点,只有我的触碰才能暂时抑制该区域的毒雾浓度,为后续的蝼蚁提供一条相对安全的通道。
而错误的路线上,则布满了增强毒性的陷阱。
代价是,每次“校准”,我都需要先吸入少量毒雾,让我的身体与迷宫产生短暂的“连接”。
校准过程中,我的感官会变得异常敏感,能清晰地感知到毒素在体内流动带来的灼烧和刺痛,尤其是腿部,像是被无数根烧红的针反复穿刺。
走对路,痛楚稍减;走错路,剧痛加倍。
这是一种酷刑。
每一次游戏开始前,我都需要先经历一遍。
用我的痛苦,为后来的蝼蚁铺路。
鼠头人说的没错,这确实是自杀。
新游戏难度大增,愿意来的蝼蚁更少了。
而每一次校准带来的痛苦,都在加速消耗我的生命。
但我不后悔。
痛苦是真实的。
但那种“掌控”自己命运的感觉,哪怕是痛苦的掌控,也是真实的。
我不再是那个只能躲在角落,靠施舍一点点善意来维持可怜自尊的“老鼠仙”了。
我在用我的命下注。
赌命之后的日子,变成了痛苦的单曲循环。
吸入毒雾,鼻腔和喉咙像是被火烧。
踏入迷宫,冰冷的铁皮贴着皮肤。
感知毒素流向,寻找那条正确的路,每一步都像踩在刀尖上,剧烈的疼痛从脚底窜上脊柱,让我几乎直不起腰。
冷汗浸透了我破烂的衣衫,和绿色的毒雾混在一起,粘腻而恶心。
我蜷缩在迷宫的角落,等待着痛苦的余波过去,等待着蝼蚁的到来。
来的蝼蚁果然少了,也更绝望了。
他们大多是真正的亡命之徒,在其他地方输光了所有,把我这里当做最后一搏的赌桌。
他们看不到我校准时的痛苦,只看到我面无表情(或者说被面具遮挡)地宣布规则,然后冷漠地看着他们在毒雾中挣扎、咳嗽、皮肤被腐蚀起泡。
“人鼠!
你这毒妇!”
“不得好死!
你和这迷宫一样恶毒!”

人鼠:终焉的赌命者番外+无删减版
推荐指数:10分
舒画舒徐是现代言情《人鼠:终焉的赌命者番外+无删减版》中涉及到的灵魂人物,二人之间的情感纠葛看点十足,作者“稚白懋懋”正在潜心更新后续情节中,梗概:在终焉之地,名字是第一个被剥夺的奢侈品。他们叫我“人鼠”,代号“子”。我是十二生肖中最卑微的起点,是无数“蝼蚁”踏入这场绝望游戏时最先踩过的垫脚石。但无人知晓,这具笼罩在鼠辈阴影下的躯壳里,囚禁着一个从现实地狱爬出的灵魂——一个被唤作“赔钱货”,连死亡都拒绝接收的弃骸。这是我的终焉,我的十日,我的嘶......
第7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