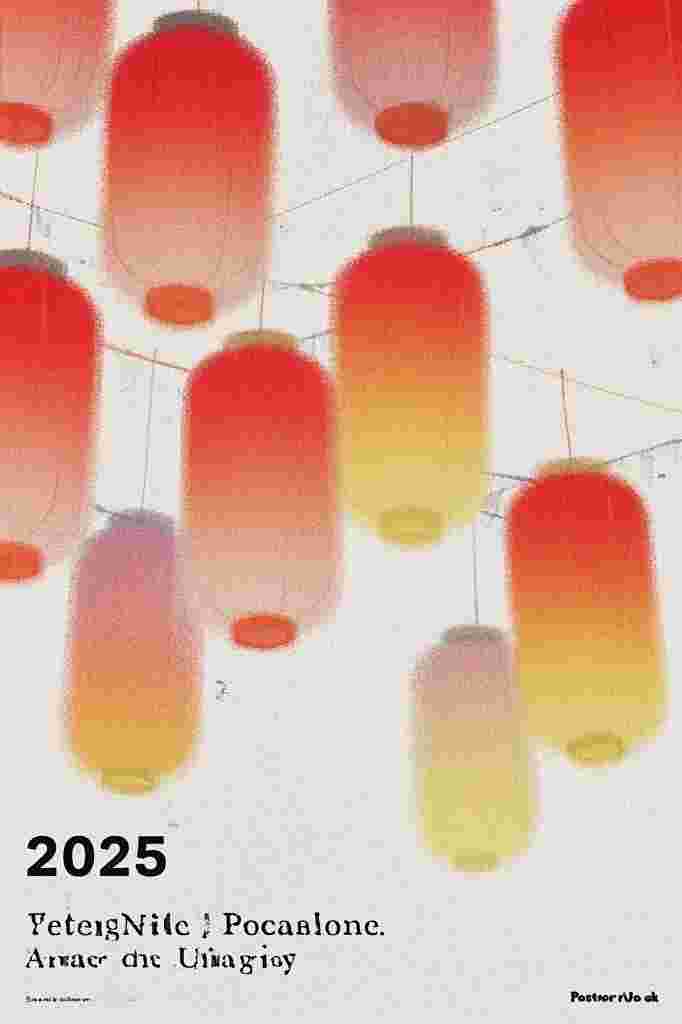栀依旧去了音乐教室。
但心情沉重,手指落在琴键上,弹出的音符也失去了往日的灵动,带着滞涩和犹疑。
窗外的江逾白几乎立刻就察觉到了不同。
今天的琴声……很乱。
错音比以往多了不少,节奏也时快时慢,透着一股明显的心烦意乱。
甚至中间停顿了好几次,只剩下空荡的寂静。
他背靠着树干,眉头不自觉地皱起。
他也听到了那些传闻,关于拆除老教学楼,关于那架钢琴的命运。
他想起那天在公告栏前看到她的样子,脸色苍白,像是被夺走了什么最重要的东西。
他心里莫名地也有些烦躁。
扯了扯嘴角,觉得自己这情绪来得有点可笑。
一架钢琴而已,一个教室而已,跟他有什么关系?
他迟早要离开这里,去打比赛,去争名次,他的世界在拳台上,而不是这些风花雪月的东西。
可是……那弹得磕磕绊绊、甚至带着点不易察觉哽咽的琴音,像细小的针,一下下扎着他心里某个地方。
妈的。
他猛地站起身,踢了一脚地上的石子。
事情爆发在周五上午。
课间操时间,教务处办公室传来一声巨响——哗啦!
像是玻璃被什么东西狠狠砸碎了。
紧接着是女人的尖叫声和男人的怒吼。
学生们像潮水一样从四面八方涌向声音来源地。
林栀也被同桌拉着,懵懂地跑过去。
教务处办公室外围得水泄不通。
透过被砸出一个大洞的玻璃窗,可以看到里面一片狼藉。
地上满是玻璃碎片,教务主任——那个以刻板和严苛著称的中年男人——正指着一个人,气得脸色铁青,手指都在发抖。
而他指着的人,是江逾白。
江逾白站在那里,下颌线绷得紧紧的,嘴角紧抿,眼神里是毫不掩饰的桀骜和怒气。
他垂在身侧的右手手背上,有几道明显的血痕,正缓缓渗出血珠。
“……无法无天!
简直无法无天!”
教务主任的声音因为愤怒而拔高,变得尖利,“江逾白!
你眼里还有没有校纪校规!
公然破坏公物!
攻击老师!
你……我没有攻击你。”
江逾白的声音冷硬地打断他,带着少年人特有的沙哑和叛逆,“我只是砸了玻璃。
而且,我说了,为什么要拆音乐教室?
那架钢琴怎么办?”
他的质问直白而莽撞,却让外围窃窃私语的人

拳击少年的钢琴曲全文+后续
推荐指数:10分
林栀江逾白是现代言情《拳击少年的钢琴曲全文+后续》中涉及到的灵魂人物,二人之间的情感纠葛看点十足,作者“南瓜汤圆汤”正在潜心更新后续情节中,梗概:“全校都知道转学生江逾白是桀骜不驯的拳击特长生,却不知道他每个周三傍晚都会躲在音乐教室窗外,听林栀弹奏那些他叫不出名字的古典钢琴曲。直到某天他为了保护音乐教室不被拆除,一拳打碎了教务处的玻璃,正在他准备接受处分时,那个总是安静得像一滴水的钢琴少女站了起来:‘如果音乐教室必须被拆除,那我也会打破一些东......
第6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