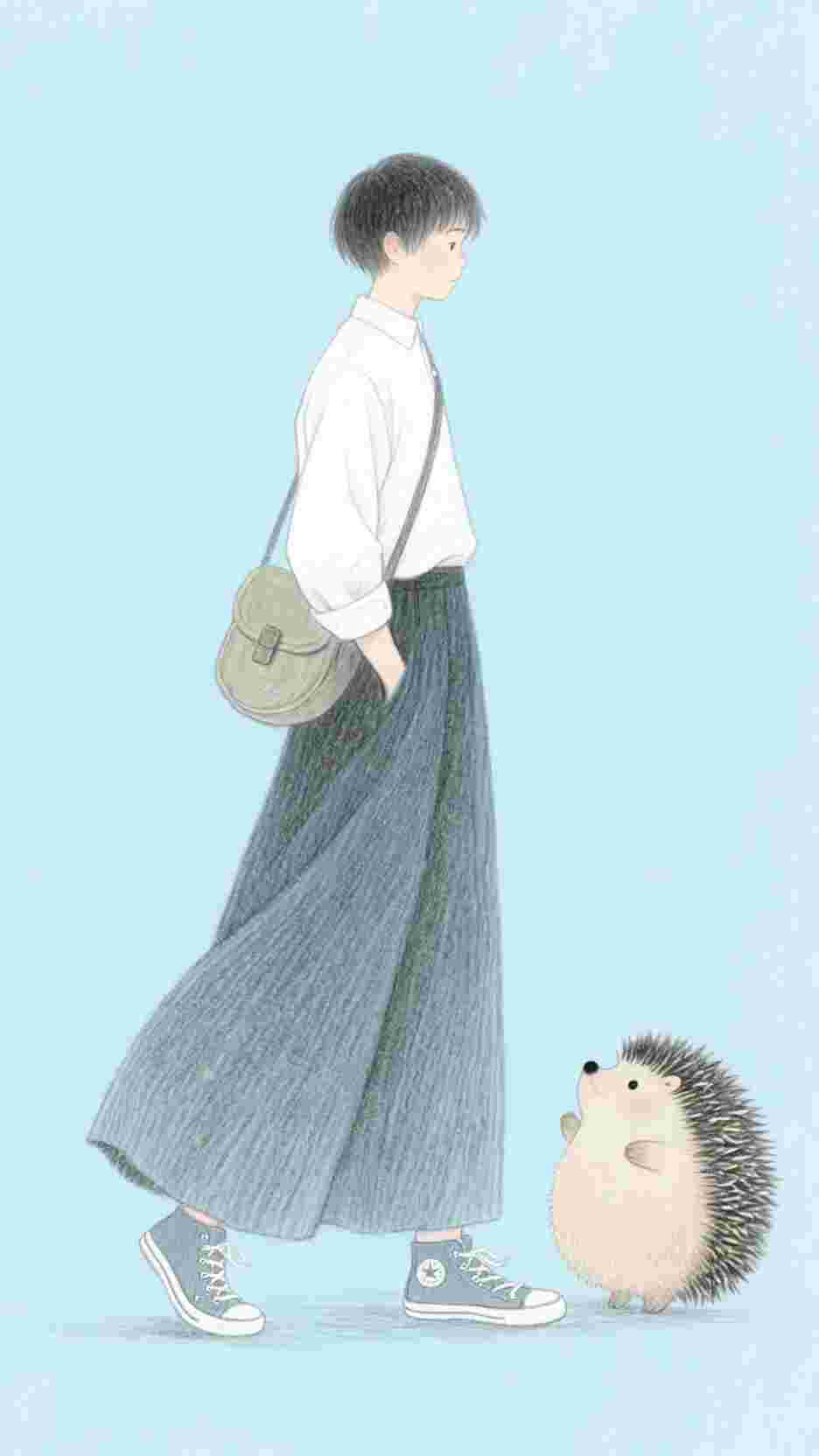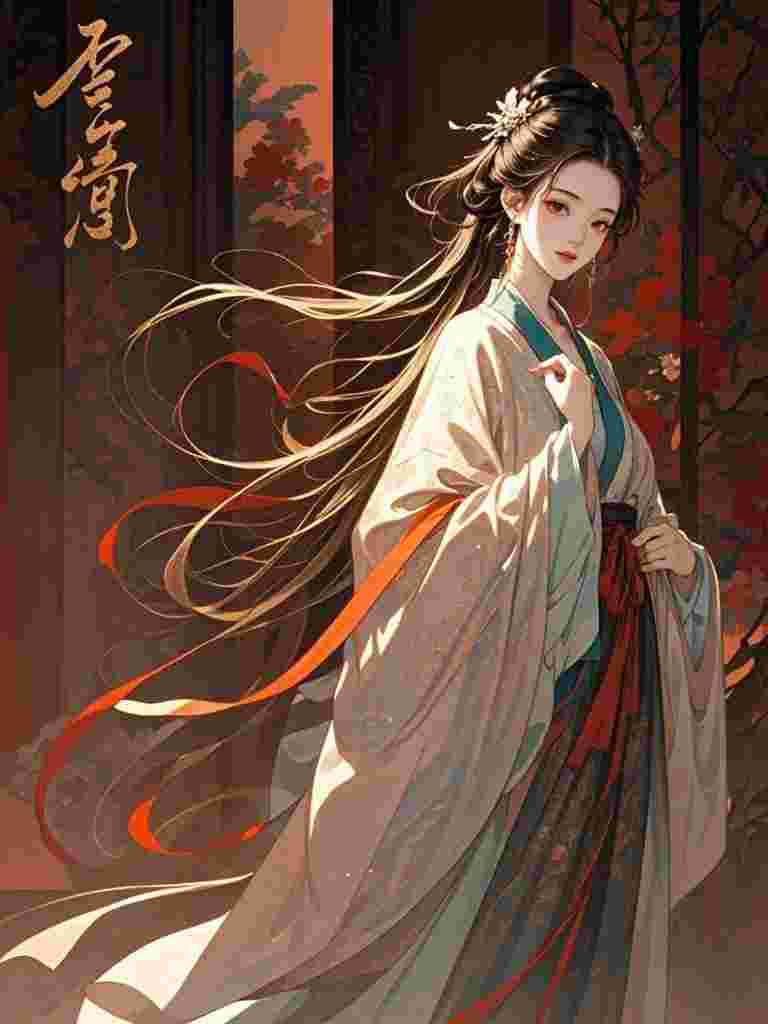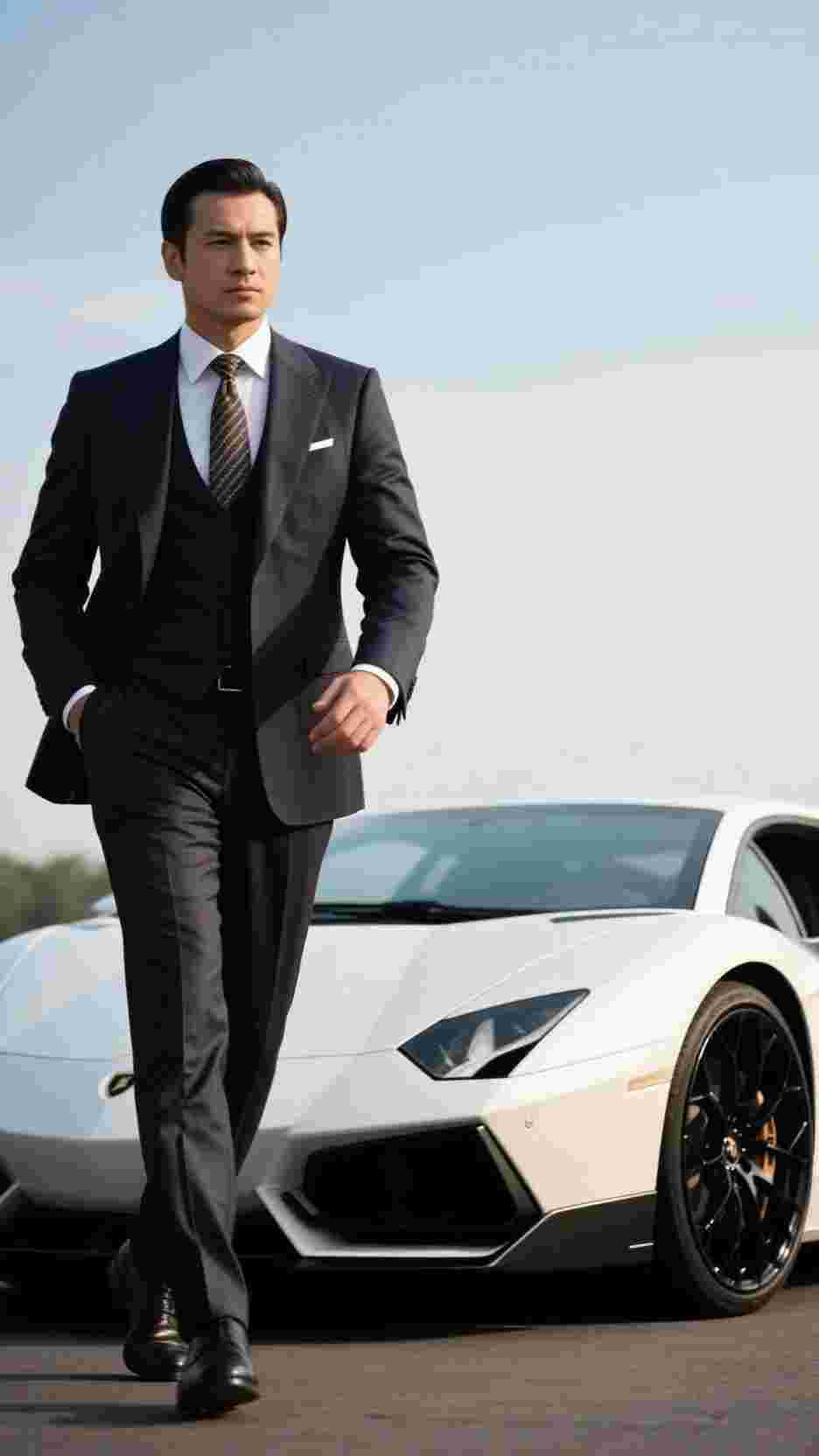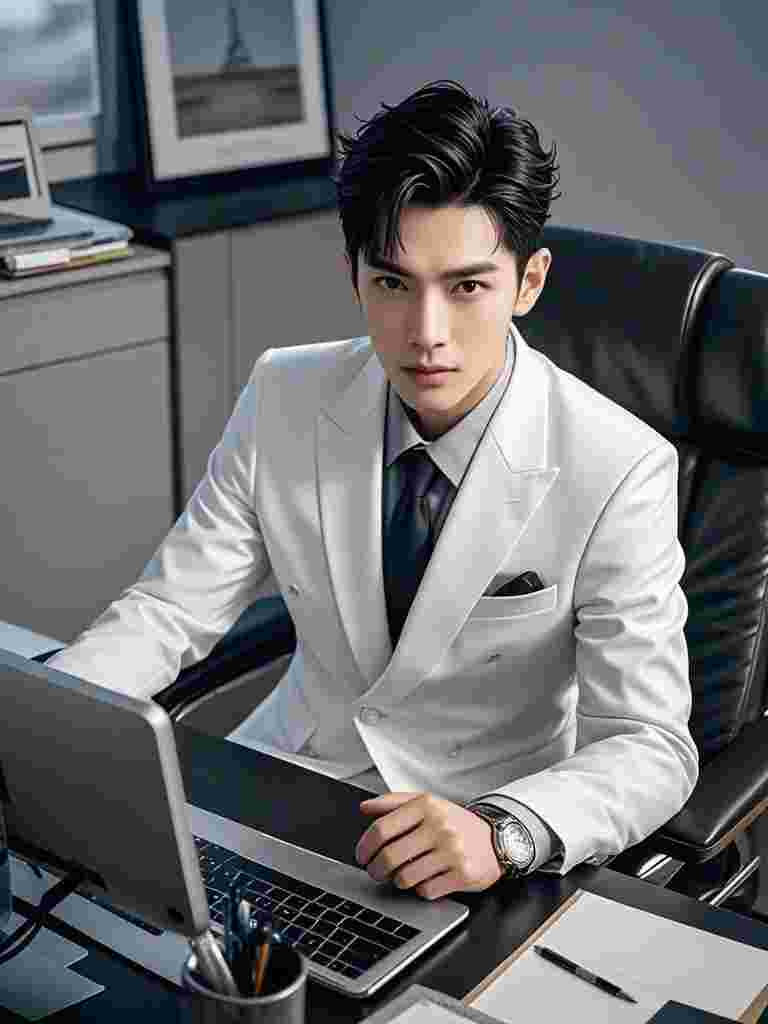枚芦苇叶戒指,在签售台后坐了整整一下午。
有读者问她:“最后那幅画里的两个人,后来去看芦苇了吗?”
林砚之握着笔的手顿了顿,然后笑了:“去了,春天的芦苇芽很好看。”
签售会结束后,她带着绘本去了古籍修复馆。
陈老先生正在修复沈知言没完成的那本古籍,见她来了,叹了口气:“知言这孩子,临走前还在念叨,说你画的芦苇缺了点什么。”
林砚之走到案前,看着那本摊开的古籍,突然明白沈知言的意思。
她从画夹里拿出一张新画,是她昨天刚完成的——湿地的芦苇荡里,站着一个孤零零的背影,手里拿着一枚铜书签,远处的天空有鸟飞过,芦苇芽在风里轻轻摇晃,却比任何时候都要鲜亮。
“我补上了。”
林砚之轻声说,“他说过,就算人等不到,总会有别的东西来。”
陈老先生看着画,抹了把眼睛:“好孩子,知言没看错你。”
那天傍晚,林砚之又去了湿地。
夕阳把芦苇芽染成了金色,她坐在湖边,打开沈知言留下的那本线装书,里面夹着一张他写的便签:“修书如修心,总要留几分缺憾,才显得真实。”
她把便签折成小小的纸船,放进湖里,看着它顺着水流漂向远方。
风掀起她的风衣,衣角扫过草地,惊起几只蜻蜓。
她低头看了看手上的戒指,突然觉得,沈知言并没有离开,他只是变成了湿地的风,变成了芦苇的芽,变成了她画里永远的光。
7 霜降(终)又是一年霜降。
林砚之在美术馆办了新的画展,主题是“等待”。
展厅中央挂着一幅巨大的《芦苇荡》,画布上,深秋的芦苇在月光下泛着白,根部却藏着密密麻麻的绿色,像无数双眼睛在眨。
画展的最后一天,陈老先生拄着拐杖来参观。
他在那幅《芦苇荡》前站了很久,说:“这画里的光,像知言身上的味道。”
林砚之笑了笑,从口袋里掏出那枚铜制芦苇书签,放在画框下。
书签的边缘已经被磨得光滑,上面刻的芦苇叶却依然清晰。
闭馆时,林砚之最后一个离开。
她走到美术馆后门的梧桐树下,看着地上的落叶,想起第一次遇见沈知言的那天,他举着伞站在雨里,说她的画里有“等”的味道。
原来有些等待,从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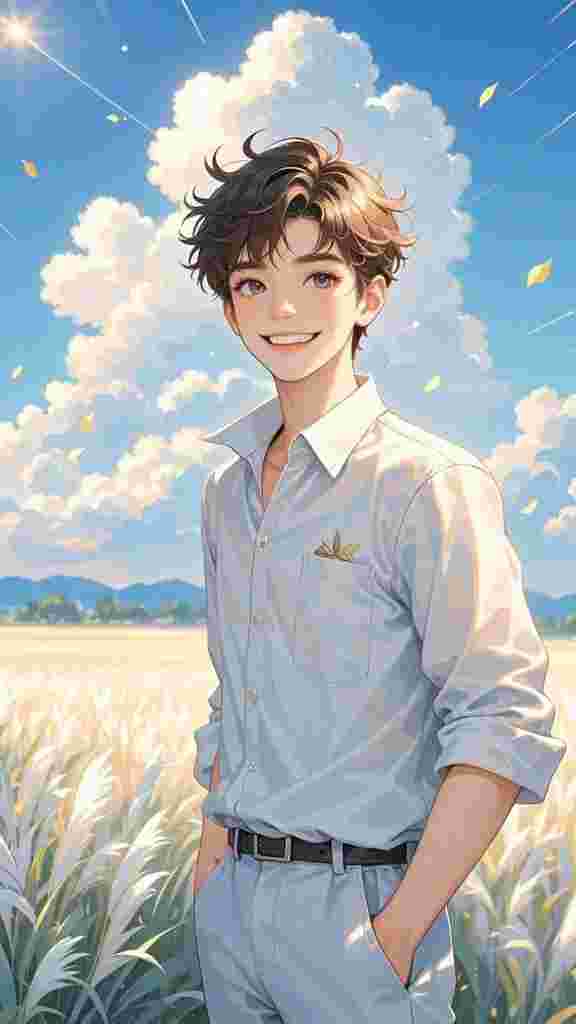
未完成的春前言+后续
推荐指数:10分
叫做《未完成的春前言+后续》的小说,是作者“祈愿缘起”最新创作完结的一部现代言情,主人公林砚之沈知言,内容详情为:1 霜降深秋的雨总带着一股子钻骨的凉,林砚之抱着刚取来的画框,站在美术馆后门的梧桐树下,看雨水把青灰色的地砖洇成深色的斑块。画框里是她刚完成的《霜降》,画布上的芦苇荡浸在冷白的月光里,每一片苇叶都像淬了冰,却在最边缘的地方留着一点暖黄,像是将熄未熄的烛火。“需要帮忙吗?”身后传来的声音带着被雨水过滤......
第8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