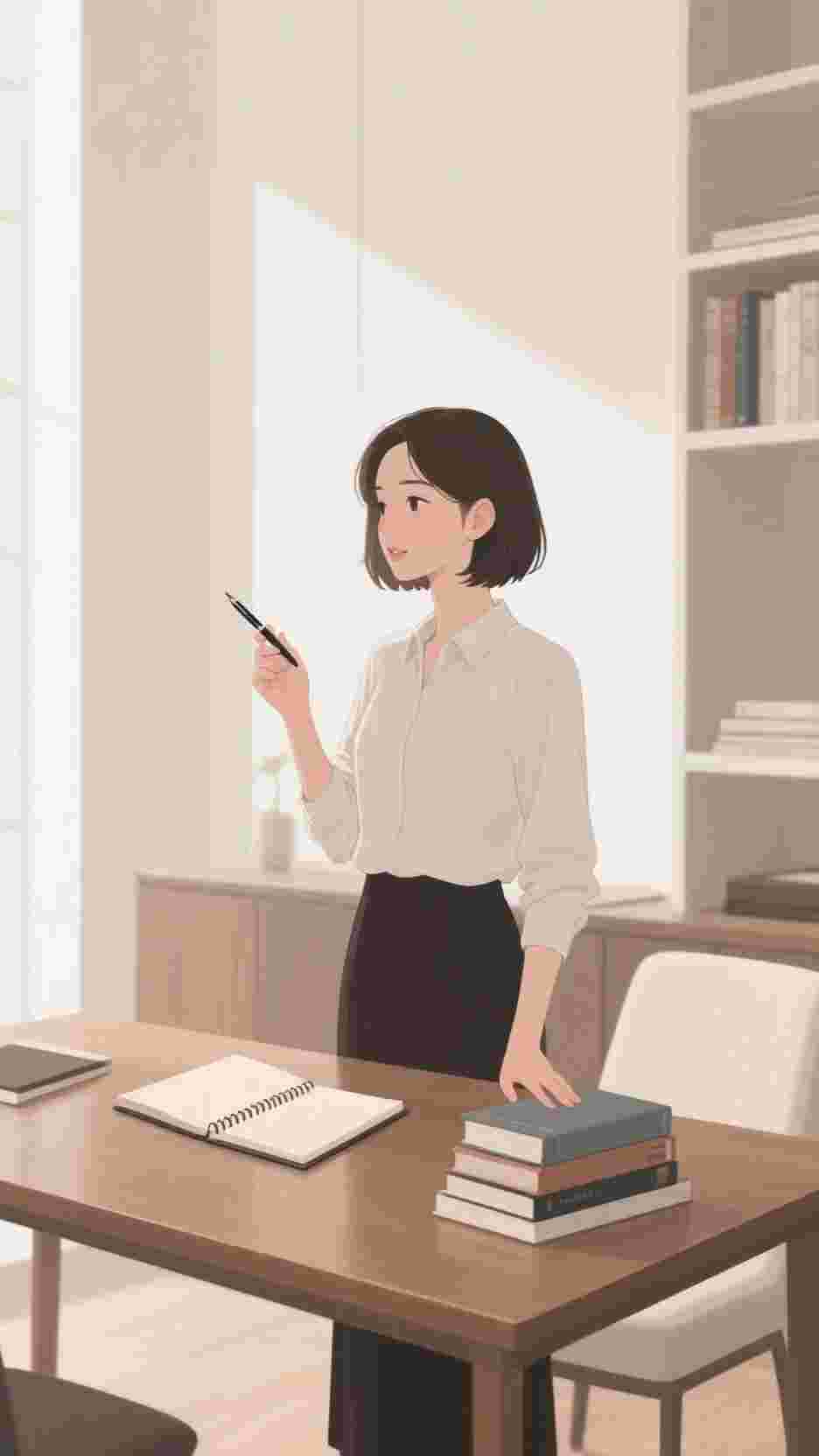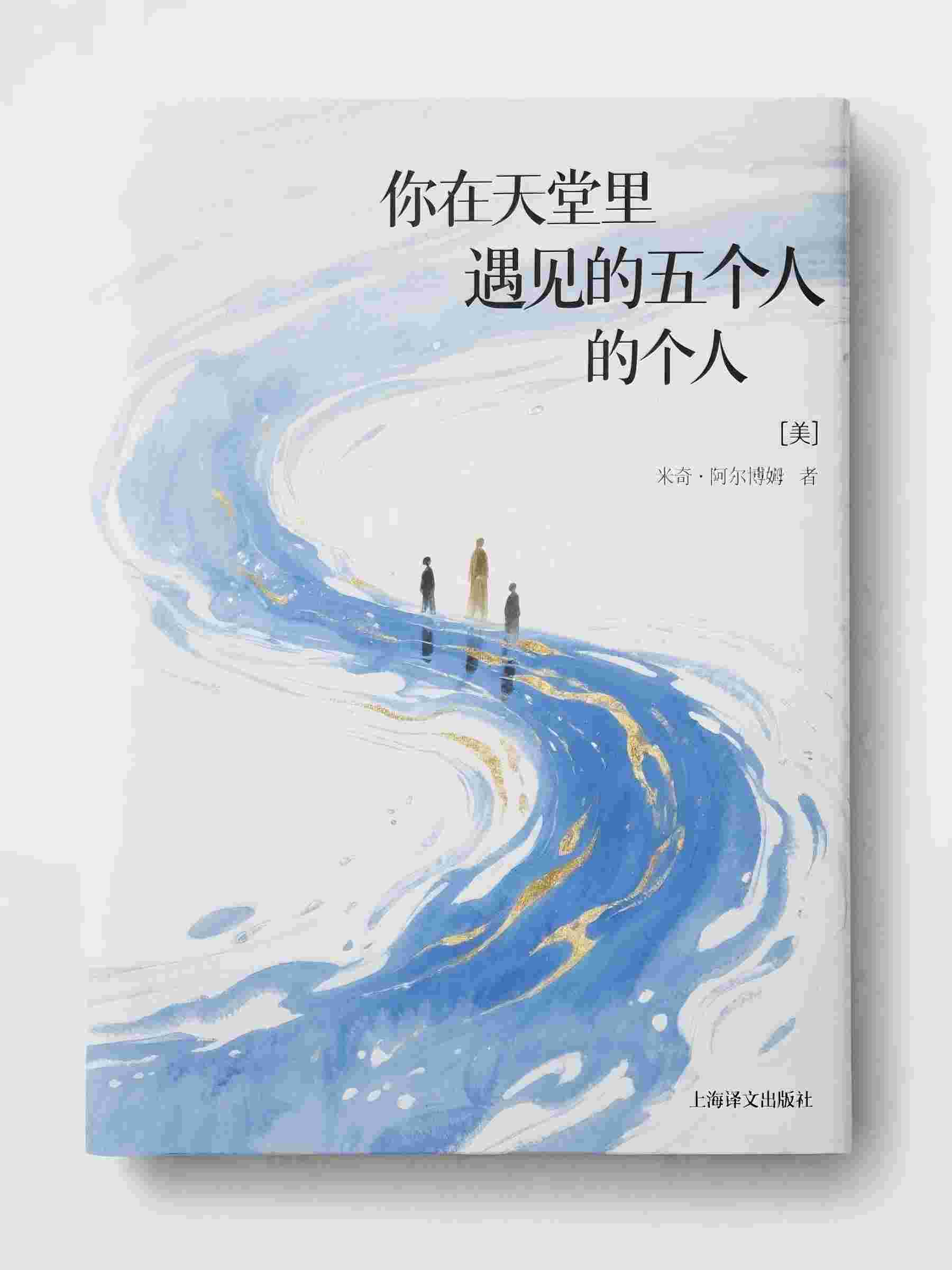时,我正给他手磨第三杯咖啡。
“林薇,下个月婚礼。”
他指尖敲了敲请柬上“苏晚”的名字,“她希望你离职。”
我盯着咖啡杯里晃动的涟漪:“八年换一张解雇通知书,陈总真慷慨。”
他忽然扣住我手腕:“苏晚的弟弟刚回国,你去见见。”
相亲对象坐在苏家老宅的紫藤花架下,白衬衫袖口卷到小臂。
他转过身,喉结上那颗红痣刺进我眼底——那是我二十二年前,送给亲生儿子的胎记。
陈添祥的订婚宴请柬飘在我办公桌上时,我刚给他手冲完第三杯曼特宁。
黑金底纹烫着“苏晚”俩字,晃得人眼晕。
“她不太适应我身边有长期合作的女性员工。”
他声音像在谈并购案,“补偿金按劳动法三倍。”
咖啡渣还在滤纸里滴水,我听见自己喉咙里挤出一声笑:“陈总,我跟您八年,就值这点违约金?”
他忽然抓住我手腕,虎口有常年握钢笔的薄茧。
苏家那个养在国外的宝贝儿子苏珩,昨天刚回国。
你去见见,算帮我个忙。
苏家老宅的紫藤花都成精了,手臂粗的藤缠住院墙,开得像个紫色瀑布。
佣人引我穿过回廊,花架下坐着个白衬衫背影,手指正百无聊赖敲着石桌。
哒,哒,哒。
和我儿子婴儿时期半夜哭闹时,我哄他拍背的节奏一模一样。
“苏少爷。”
我嗓子里像卡了把咖啡渣。
年轻人转过身,阳光跳进他领口,喉结上那颗朱砂痣红得刺眼——二十二年前我亲手给新生儿洗澡时,还以为那是沾到的血渍。
“林薇小姐?”
苏珩挑眉看我,虎牙在唇边硌出个小尖角,“我姐说你是人间绝色,果然没骗我。”
我指甲掐进掌心才没去摸他喉结。
陈添祥的声音突然炸在背后:“林秘书倒会找地方偷情。”
他攥着我胳膊往车库拖,眼底结着冰:“苏珩才二十二!”
“陈总终于想起关心员工私生活了?”
我挣开他,后腰撞上奔驰车门,“当年您亲手把我儿子送走时,怎么不嫌他小?”
玻璃车库顶棚突然炸开蛛网裂痕。
苏晚举着高尔夫球杆站在阴影里,绸缎裙摆沾着草屑:“我说过别碰我弟弟。”
苏珩把我拽到身后时,我闻到他领口松木香里混着奶味——和他婴儿时期用的爽身粉一个味道。
陈添祥的订婚宴

狗贼今天也在骂朕吗结局+番外
推荐指数:10分
小说《狗贼今天也在骂朕吗结局+番外》,超级好看的现代言情,主角是李炽楚卿,是著名作者“景三Yying”打造的,故事梗概:陛下每日上朝第一问:“楚爱卿今日可有骂朕?”我伏地叩首:“臣今日休沐。”龙椅上传来一声冷笑:“那就是骂了双份,留着明日一起奏?”满朝文武死死憋笑,只有我知道——李炽这狗皇帝,是在报复我今晨往他茶盏里吐口水未遂。寅时三刻,天还黑得像泼了墨,御史台的更鼓已催命似的敲了三遍。我叼着半块冷透的胡麻饼,一脚踹......
第6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