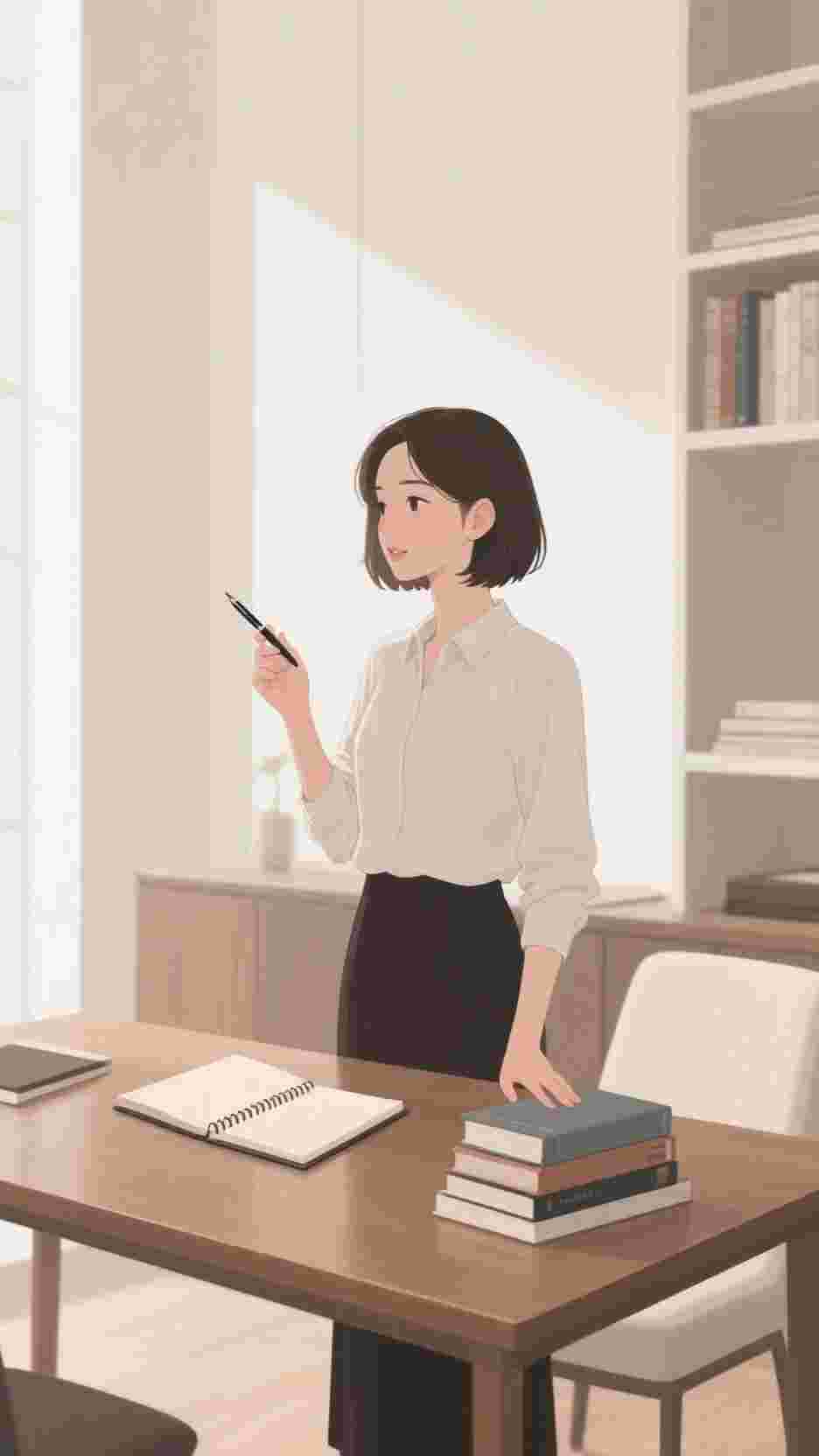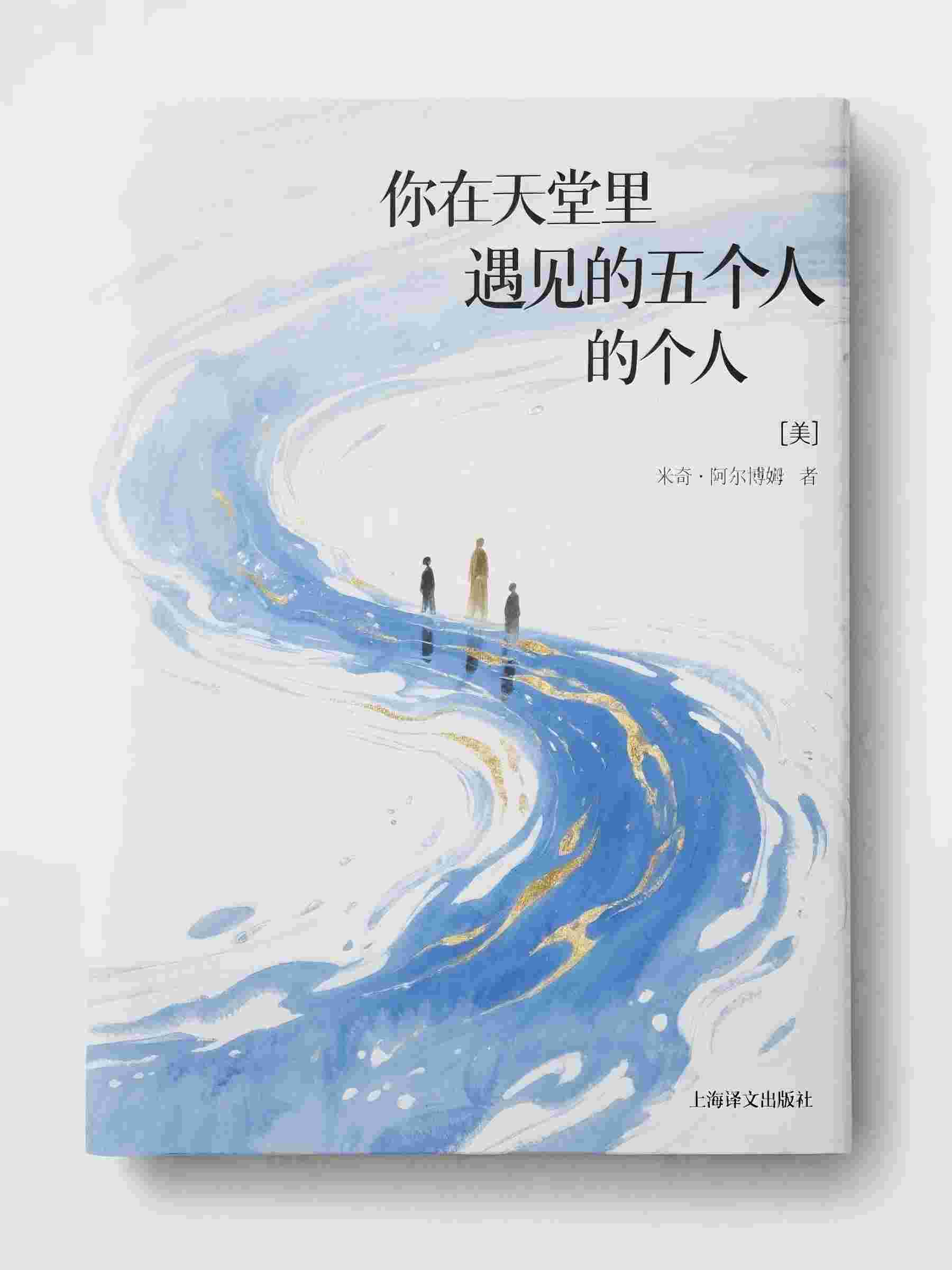!”
他如临大敌,急得脸色都红润几分。
“婚姻大事向来是父母之命,媒妁之言。
我与姑娘萍水相逢,这实在于礼不合!”
我佯作困惑。
“不是你说双亲都不在了吗?
正好我爹娘也过身了。
挑个好日子,咱俩就洞房吧!”
“不,不,在下的意思是姑娘清白人家,某一介白身,身无长物,唯恐耽误了姑娘!”
“好了,别磨磨叽叽的!
你要不乐意,现在就走罢。
反正救你一命,我已是仁至义尽了。”
我板起脸,只觉越发口干舌燥,索性小口喝起鱼汤,不敢直视谢芸。
可屋子里太安静了,我按捺不住,用余光偷偷觑了他好几眼。
谢芸就静静地靠在床头,垂着眼眸。
像一池深秋的静水,难以捉摸。
热气凝成的小水珠沿着他挺拔的鼻梁、秀气的鼻尖一路滑下,“滴答”落在单薄的被衾上。
略带探究之意的目光忽然落在我身上,我挺直腰板,紧张地与他对视。
澄澈如井的眸子里,分明映照着我的身影,还有一片温和又疏离的幽深。
仿佛斟酌了一番,数日粒米未进的他,还是选择为鱼汤折腰。
见他总算有所动作,我立马出声询问。
“那咱俩的婚事,你是答应了?”
颇有一副威逼利诱良家妇男出卖色相的鸨母作态。
“嗯。”
细若蚊呐。
我满意地点头,决定明日便去父母坟前烧些纸钱,好让他们在地下也知晓,女儿就要成家了。
其实,仓促订下婚事并非单纯见色忘利,实乃形势所逼。
再有两个月,我便年满十六。
按照大昱律例,十六周岁还未婚嫁的女子需要缴纳五算税,也就是五倍的赋税。
这于爱财如命的我而言,与要命无甚区别!
鉴于谢芸伤还没好,我只好委屈自己,又在竹椅上囫囵过一夜。
月色皎洁,照得屋内如雪洞般明亮。
我不适应新“床”,久久难以入睡。
听着不远处平稳的呼吸声,满腔无名怒火。
几乎瞬间便决定,“准夫妻”也要有难同当。
“你睡了吗?
陪我说说话吧。”
隐约传来一声无奈的叹息。
可能是错觉吧。
“姑娘想聊什么?”
“你说的重金是多少金啊?”
整个白日,我被这句话吊得七上八下,都无心干活了。
声音闷闷地从被子里传来。
“阿福姑娘不是要我以身相许吗?”
“为人处事自

村姑阿福前言+后续
推荐指数:10分
现代言情《村姑阿福前言+后续》,现已上架,主角是抖音热门,作者“谢青林”大大创作的一部优秀著作,无错版精彩剧情描述:捡回家的美貌夫君竟是太子?上得厅堂,下得厨房,睡得龙床,实乃贤夫表率!无痛当皇后,天姿平平,全凭运气!且看一介贪财好色小村姑“顺”袭之路。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我本是一个山野村姑。幼年失怙,为让双亲入土为安,家中仅有的薄田也换了三寸桐棺。老乡长瘦骨伶......
第4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