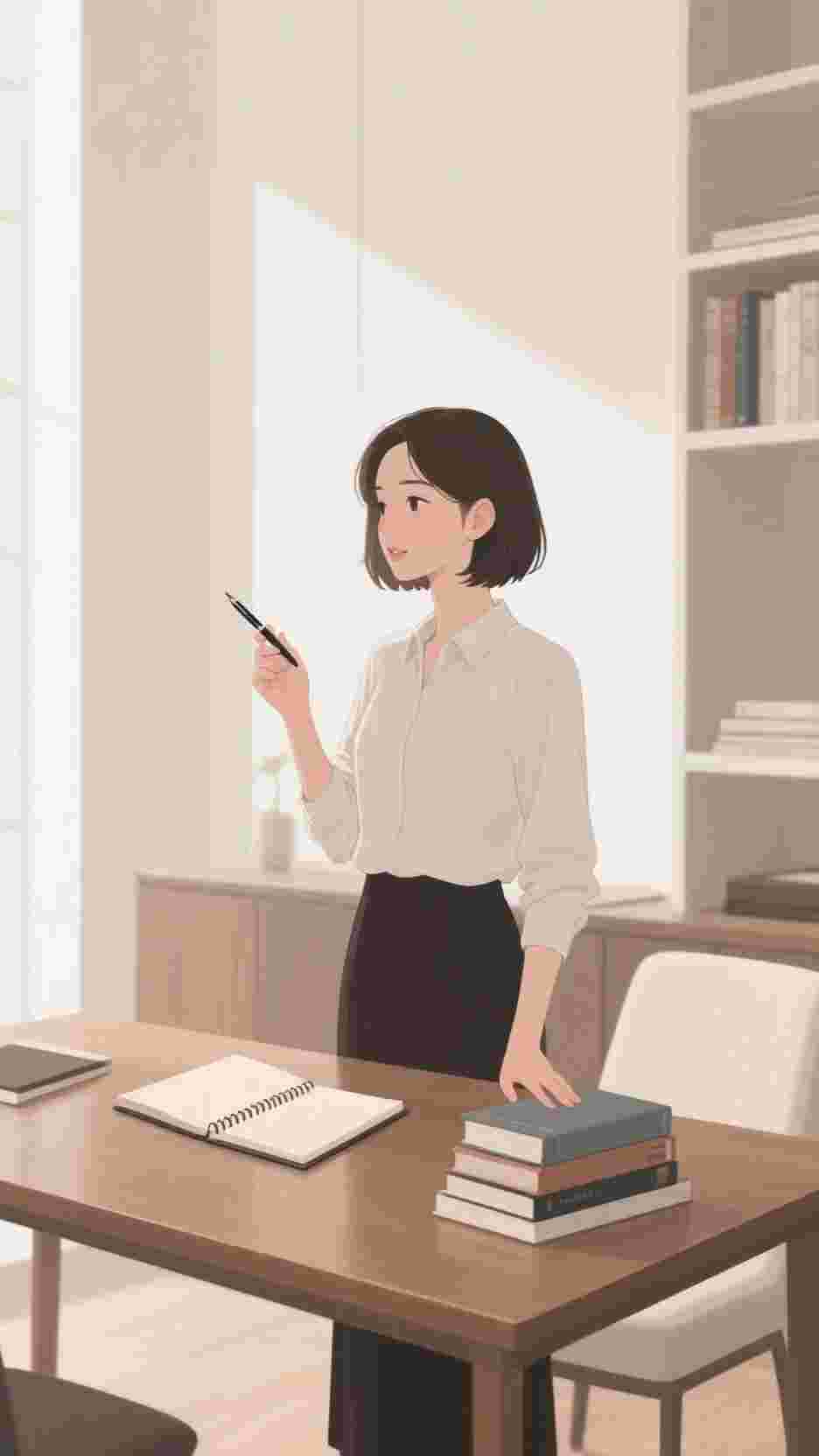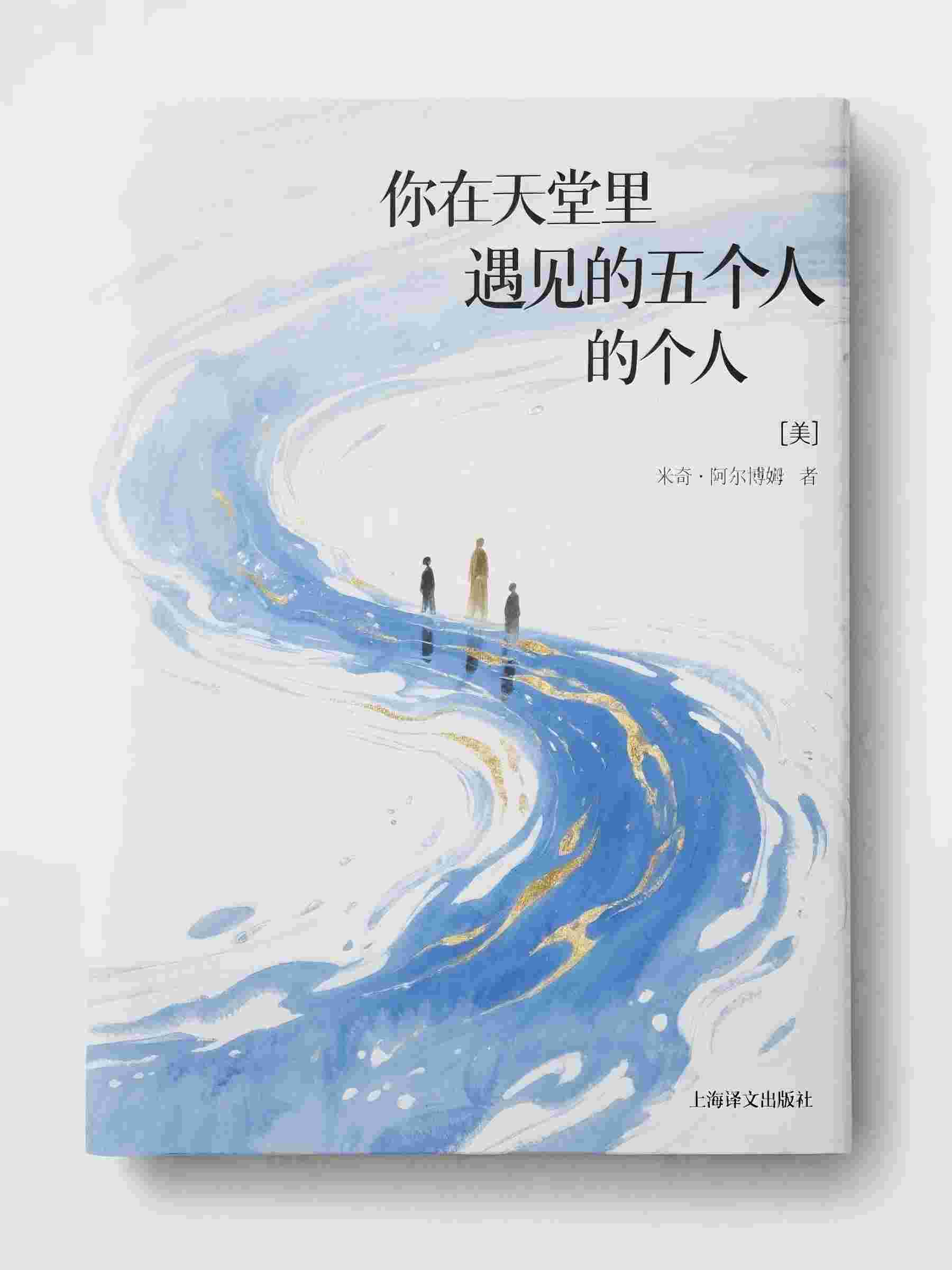出。
杯中冰水纹丝未动,一如七日前地牢外那截玄色衣角,离她伸来的手不过三寸,却再未靠近。
“传令下去,”我说,“就说她知晓北狄通商密道,若泄露,边关三州将无险可守。”
影七领命而去。
不到半日,刑场外人头攒动,烂菜叶与碎石堆在木台下,像祭台前供奉的秽物。
午时将至,沈清梧被押上刑台。
囚车栅栏早已被砸裂,她左颊肿起,发间缠着菜叶,右眼仅存的光映着台下举着的“妖女”木牌。
周明礼站在茶楼二层,掀开竹帘,正欲开口,三枚铜钱破空而至,钉入他脚前三寸青砖。
我从檐下走出,玄色蟒袍未沾半点雨水。
文臣们噤声,我举杯向那茶楼方向示意。
周明礼面色铁青,却再未出声。
圣旨来得极准,午时三刻,黄卷由内侍捧至台前。
我亲手展开,明黄绸缎在雨中微微发胀。
“奉天承运,皇帝诏曰:沈氏清梧,虽涉逆案,然查无实据,免死罪,贬为浣衣局官婢,永不得赦。”
话音未落,她猛地挣脱枷锁,扑向台边。
影七未拦,任她滚落泥中。
她用肘撑地,十指早已碎裂,掌心翻出白骨,每爬一寸,青石便留下血痕。
我缓步走下台阶,手中执伞,伞沿压低,只让她看见蟒袍下摆的四爪金纹。
“王爷……”她嗓音如砂石磨过铁器,“清梧知错了。”
我蹲下,指尖拂过她手腕那道旧疤——当年她为我挡箭所留。
如今皮肉翻卷,已不成模样。
“十年前你递伪证时,可想过今日?”
我问。
她剧烈咳嗽,血沫溅在石板上,被雨水冲成淡红。
我起身,靴尖碾住她发间金钗,轻轻一踏,钗身断裂,半截刺入泥中。
她未哭,只是抬头,右眼映着灰沉的天光。
第二道圣旨来时,雨势更急。
李德全捧着金漆托盘,脚步微滞。
我接过卷轴,未看,直接抛入雨幕。
“告诉陛下,”我说,“摄政王府不是教坊司。”
李德全垂首,拂尘轻扫她肩头:“沈娘子,王爷特批您住西厢房。”
她猛地抬头,眼中竟有一瞬亮色。
下一刻,两列玄甲军抬着木盆列队而出。
盆中衣物浸着冰碴,是百件未洗的官服。
“从今日起,”我解下腰间白玉错金佩,掷于她脚边,“每日卯时前洗完。
洗破一件,抽十鞭。”
她盯着

穿书大反派后,我任由女主落难全文+番茄
推荐指数:10分
长篇现代言情《穿书大反派后,我任由女主落难全文+番茄》,男女主角谢琰沈清梧身边发生的故事精彩纷呈,非常值得一读,作者“桃子快到怀里来”所著,主要讲述的是:我穿成谢琰那天,正逢大雪。他是权倾朝野的摄政王,也是书中必死之人。原主痴迷女主沈清梧,助她扶帝登基,反被鸩杀雪夜。我冷笑:这情劫,我不入。她落难,我闭门。她求援,我焚书。昔日她弃我如敝履,今日我冷眼观她坠深渊。朝堂如棋,人心似冰。谢琰已死,活下来的,是看透因果的局外人。清梧啊,你曾说我狠。可你不知,......
第10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