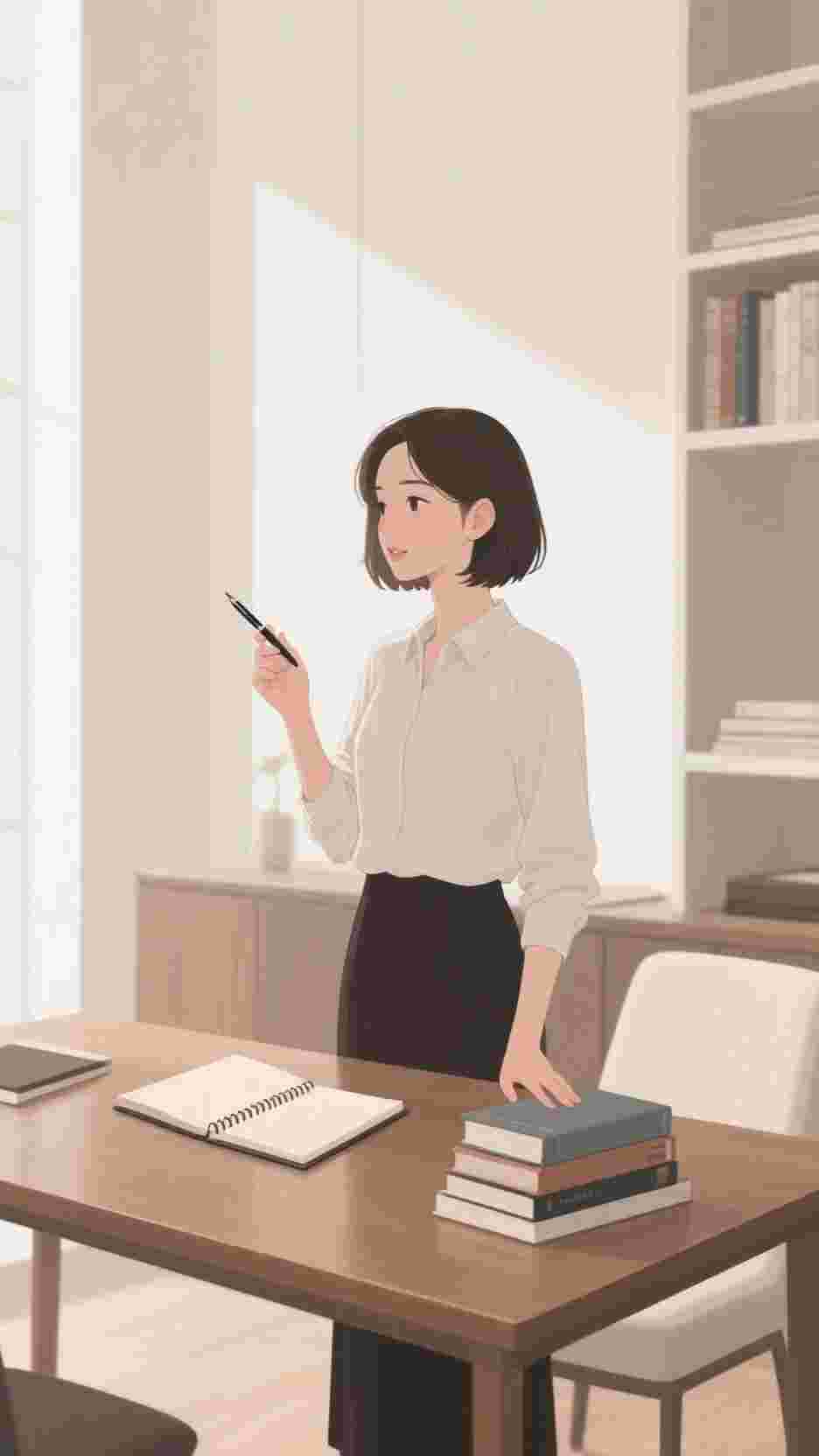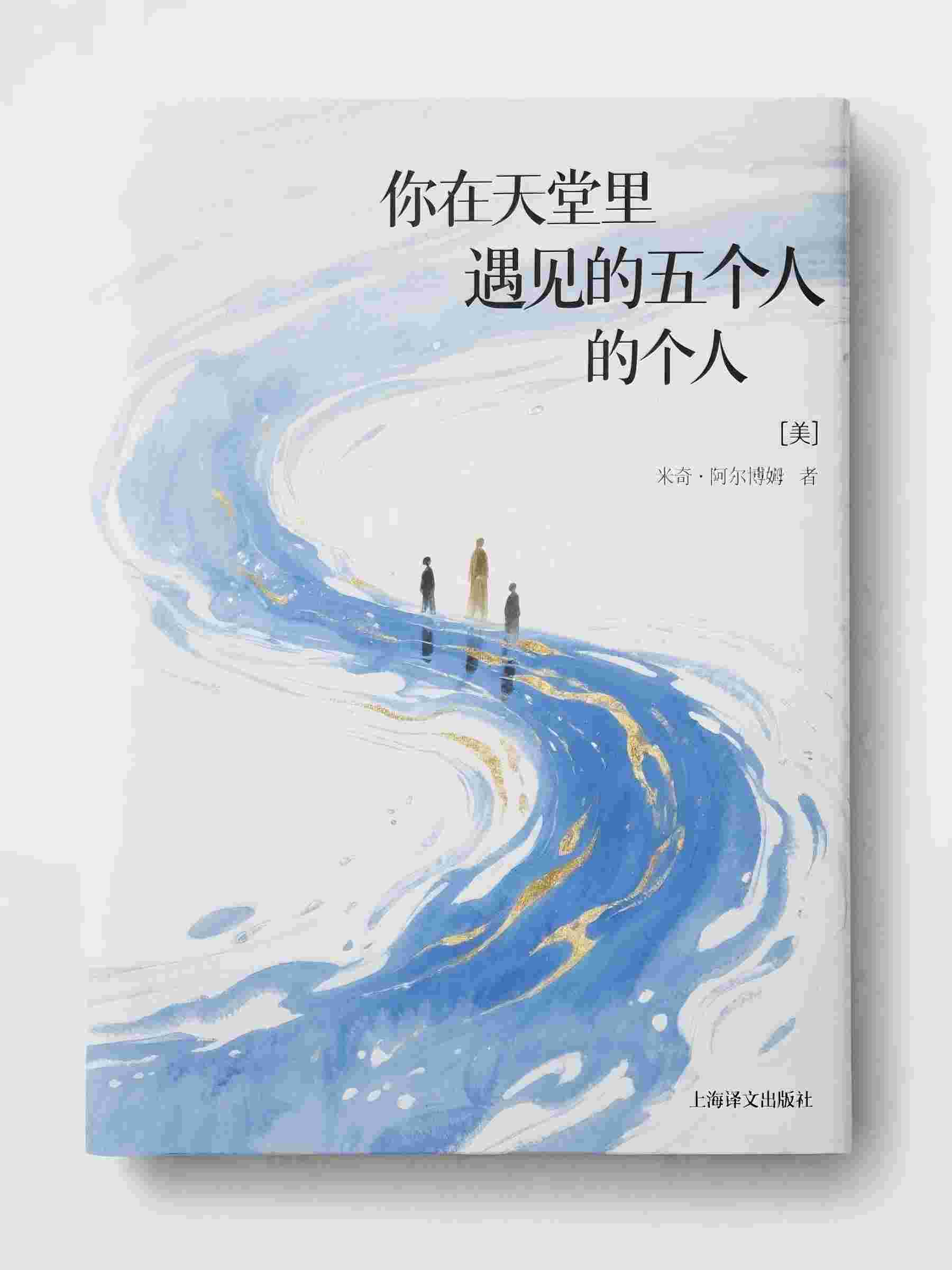那玉佩,许久,忽然笑了。
笑声混着雨声,断断续续,像风中残烛。
百姓围在府门外,有人高喊:“妖女不死,国运难昌!”
我转身,命影七提来三桶冰水。
第一桶泼下时,她浑身一颤,发丝紧贴面颊,露出左眼那道刀疤——赵崇远所赐。
第二桶泼下,她膝行向前,额头触地,叩首。
第三桶,我亲自提起。
水从头顶浇落,冰碴滑入她衣领,她打了个寒噤,却仍伏在原地。
“你听好了。”
我拽紧缰绳,照夜玉狮子不安地踏了踏蹄。
围观者屏息。
“谢琰从未欠过沈清梧什么。”
我扬鞭,抽在门环上,青铜兽首发出刺耳鸣响,“从你递出伪证那日起,我们便两清了。”
马蹄声起,我策马欲行。
身后忽传来笑声,比先前更响,更疯。
我回头。
她跪在泥水中,断指抠住门缝,指甲翻卷处渗出血丝。
雨水顺着伤口流下,混着泥浆,在青石板上画出歪斜的线。
袖中那半片烧焦的纸页悄然滑落,正是《平戎策》残页。
她曾为我抄录三遍,字迹清秀如初雪。
如今纸页泡在水中,墨迹晕开,像一团化不开的黑血。
她抬头望我,右眼映着朱雀大街尽头的暮色。
我勒住缰绳。
她忽然开口,声音极轻:“那年春宴,你曾说……愿与我共赏十年梅花。”
6卯时未到,浣衣局的井水已结了层薄冰。
她跪在石阶上,十指泡在木盆里,指尖泛着死灰,虎口裂开的口子渗出血丝,顺着冬衣的粗布纹路蜿蜒而下。
女官将一摞浸透冰水的官袍砸在她膝前,声音冷硬:“今日若洗不完,鞭数翻倍。”
她没抬头,只将冻僵的手指蜷了蜷,指甲翻卷处嵌着碎石。
昨夜抄写的《女诫》摊在墙角,纸页被血水浸透,边缘用碎瓷片划出的“谢琰”二字,已被巡夜人发现。
周明礼的弹劾奏章已递入御前,称她“妖心未死,当焚其书,断其手”。
她忽然抓起木盆,砸向石阶。
瓷片碎裂,额角被划开一道血口,血顺着眉骨流下,模糊了右眼那道刀疤。
她盯着地上的残片,想起七日前他掷玉佩的姿态——不带一丝迟疑,不落半分温度。
次日清晨,她被调往东宫。
太子书房外,铜铃在风中轻响,锈迹斑驳,声不如王府檐角那般清亮。
她捧着一叠新浆洗的

穿书大反派后,我任由女主落难谢琰沈清梧全文免费
推荐指数:10分
以谢琰沈清梧为主角的现代言情《穿书大反派后,我任由女主落难谢琰沈清梧全文免费》,是由网文大神“桃子快到怀里来”所著的,文章内容一波三折,十分虐心,小说无错版梗概:我穿成谢琰那天,正逢大雪。他是权倾朝野的摄政王,也是书中必死之人。原主痴迷女主沈清梧,助她扶帝登基,反被鸩杀雪夜。我冷笑:这情劫,我不入。她落难,我闭门。她求援,我焚书。昔日她弃我如敝履,今日我冷眼观她坠深渊。朝堂如棋,人心似冰。谢琰已死,活下来的,是看透因果的局外人。清梧啊,你曾说我狠。可你不知,......
第11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