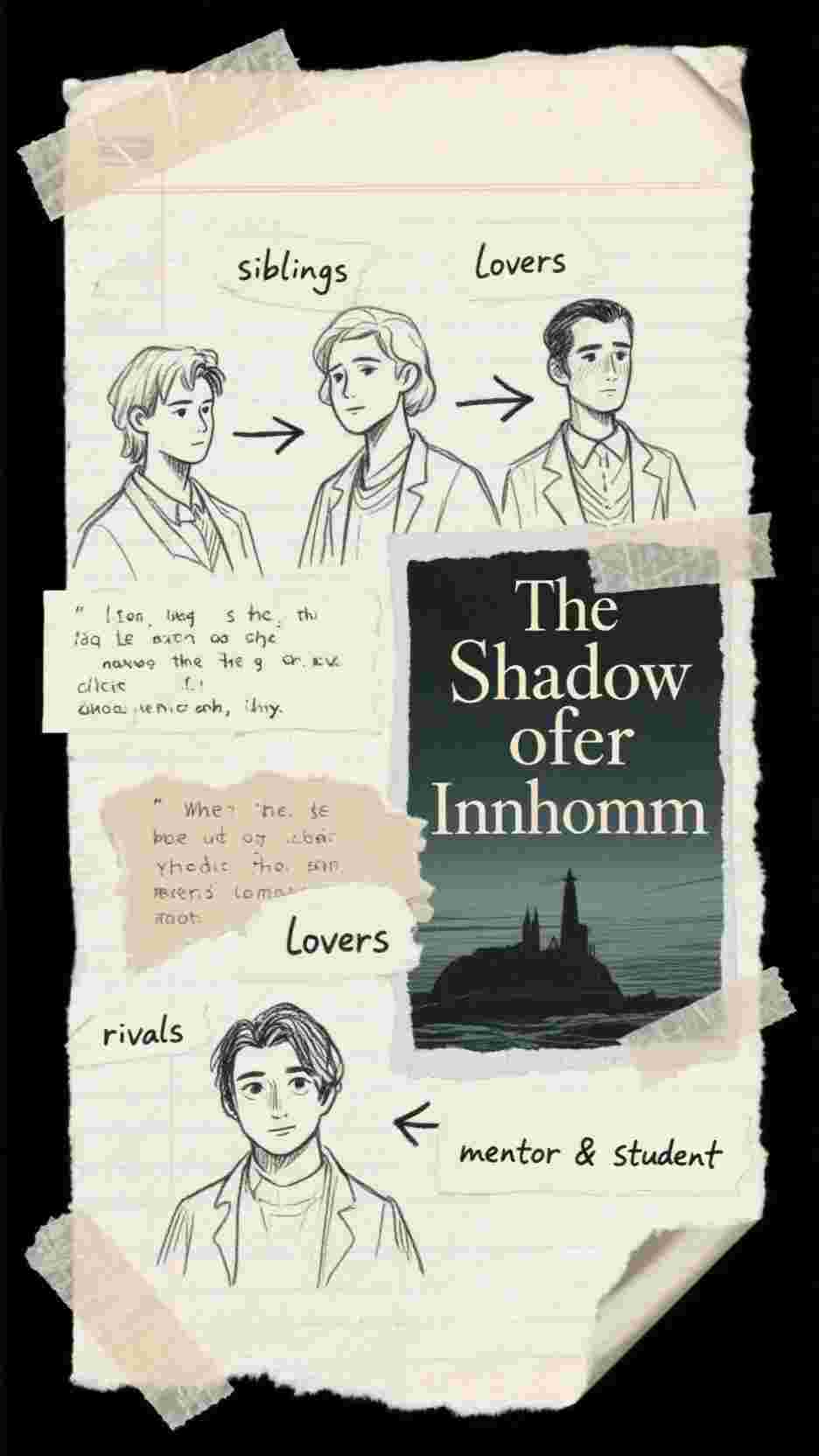水槽里还有早上用过的碗,没洗。
我打开水龙头,热水流出来,带着铁管的震动。
我伸手试了试水温。
水流冲进瓷碗,泡沫慢慢浮起。
6水还在流,我关了水龙头,碗底残留的泡沫顺着瓷壁滑下去。
厨房灯是暖黄的,照在洗碗布上,那块布边缘已经有些发硬。
我把它挂回水槽边,顺手擦了手。
手机在裤袋里震了一下。
没看内容,我知道是谁发的。
周知遥约我江边见,说有话谈。
我换了件干衬衫,袖口那点铅笔灰没擦,也没换。
出门前看了眼玄关,红本还在柜子上,封面朝上。
许昭的防水袋不见了,她早上走时带走了证件。
雨停了,风还凉。
我撑开伞,走下台阶。
江堤的路湿,踩上去有轻微的吱声。
远处货轮的灯在江面划出一道晃动的光,像被撕开的锡纸。
他站在观景台尽头,背对着江,风衣领子竖着,一只手插在口袋里。
看见我走近,没动。
“你来得比我想得快。”
他说。
我没应。
收了伞,靠在栏杆上。
伞尖滴水,一滴一滴砸在水泥缝里。
“你觉得你做得对?”
他看着我,眼神不冷也不热,“娶她,是为了证明什么?”
“不是为了证明。”
我说。
“那是为了报复?”
他嘴角动了动,“让许澜看见,她不要的,别人抢了?”
我摇头,“她没不要我,是她选了别人。
我也没抢,是许昭一直在。”
他皱眉,“你就因为这些——她给你倒姜茶,记得你胃寒?
这些事,谁都能做。”
“但她做了十年。”
我看着江面,“你写诗的时候,她在记我几点下班;你念‘灵魂相认’的时候,她在想我昨天熬夜,肩膀是不是又僵了。”
他没说话。
“我不需要灵魂震颤。”
我继续说,“我要的是,早上醒来,有人问我粥要不要再热一下;下雨了,伞会多带一把。
这些事很小,但十年下来,就成了我活着的底子。”
他盯着我,“所以你结婚,是因为感激?”
“不是感激。”
我转头看他,“是安心。
她不追着我说爱多深,但她每天都在。
我累的时候,她不说‘加油’,只递一杯温水。
她不替我做决定,但会在我犹豫时,轻轻说一句‘你想怎么过,我都陪着’。”
江风卷着湿气扑上来,我顿了顿,“我以前以为,爱是

求婚被截胡,我转身直接娶她姐前文+后续
推荐指数:10分
书荒的小伙伴们看过来!这里有一本“桃子快到怀里来”创作的《求婚被截胡,我转身直接娶她姐前文+后续》小说等着你们呢!本书的精彩内容:梅雨季的梧桐巷,青石板泛着光。我蹲在茶馆屋檐下,给许澜擦鞋。五年了,她连伞都懒得和我共用。戒指在口袋里发烫,像块烧红的铁。她说:“等周知遥回来再说。”我笑出声。白月光回来了,我就该让位?可她不知道,江边那栋旧书坊二楼,有个人,一直看着我。她说:“陈砚,你值得更好的。”那天,我转身走向了许昭。1梅雨季......
第12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