她带来的生机。
“我以为我死了,”他声音干涩,带着劫后余生的颤抖,“掉下去的时候…脑子里只有你的脸。”
那一刻,沈知遥构筑了数月的防线土崩瓦解。
她照顾他复健,陪他做枯燥的理疗,看他因为疼痛和挫败而暴躁摔东西,再默默收拾干净。
他笨拙地学习表达:“今天的汤…很好喝。”
“理疗师说…我手指恢复得不错。”
甚至在她生日那天,他穿着不合身的衬衫,捧着一小束有点蔫了的向日葵,出现在她公寓门口,生硬地说:“以后…有保护绳也行。”
他笨拙地尝试走进她的平原,像一个习惯了悬崖峭壁的登山者,第一次踏入平坦却陌生的土地,每一步都带着试探和小心翼翼。
沈知遥贪恋着这份笨拙的温暖,仿佛只要他愿意系上那根“安全绳”,深渊就可以被填平。
裂痕从未真正弥合,只是被小心翼翼地掩盖。
初夏,学校组织毕业班去云雾山露营。
沈知遥带班,陈野作为“有野外生存经验”的家长志愿者随行。
入夜,篝火燃起,学生们围坐唱歌。
陈野独自坐在营地边缘一块凸起的岩石上,眺望着远处被月光勾勒出冷硬轮廓的山脊线,眼神是沈知遥久违的空旷与渴望。
“想爬?”
沈知遥走过去,递给他一杯热水。
他接过杯子,指腹无意识地摩挲着杯壁:“嗯。
那岩壁…很漂亮。
月光下,像流动的水银。”
他的声音带着一种近乎痴迷的沉醉。
沈知遥的心一点点沉下去。
她在他身边坐下,肩膀挨着他的肩膀,试图汲取一点温度。
“陈野,” 她声音很轻,像怕惊飞什么,“我们以后…就在平地上走,不好吗?
买个小房子,周末看看电影,逛逛公园…”陈野的身体几不可察地僵硬了一下。
他沉默地喝了口水,热气氤氲了他深邃的眼眸。
“知遥,”他开口,声音低沉而遥远,“我试过了。
真的。
但每天挤在人群里,看着一样的风景,听着一样的话…我觉得自己像个被拔掉电池的钟,指针还在动,心已经停了。”
他转过头,月光照亮他眼底压抑的痛苦和坦诚,“那不是活着,是等待死亡。”
沈知遥看着他,清晰地听到了某种东西碎裂的声音。
那是她精心维持的、关于妥协与融合的幻梦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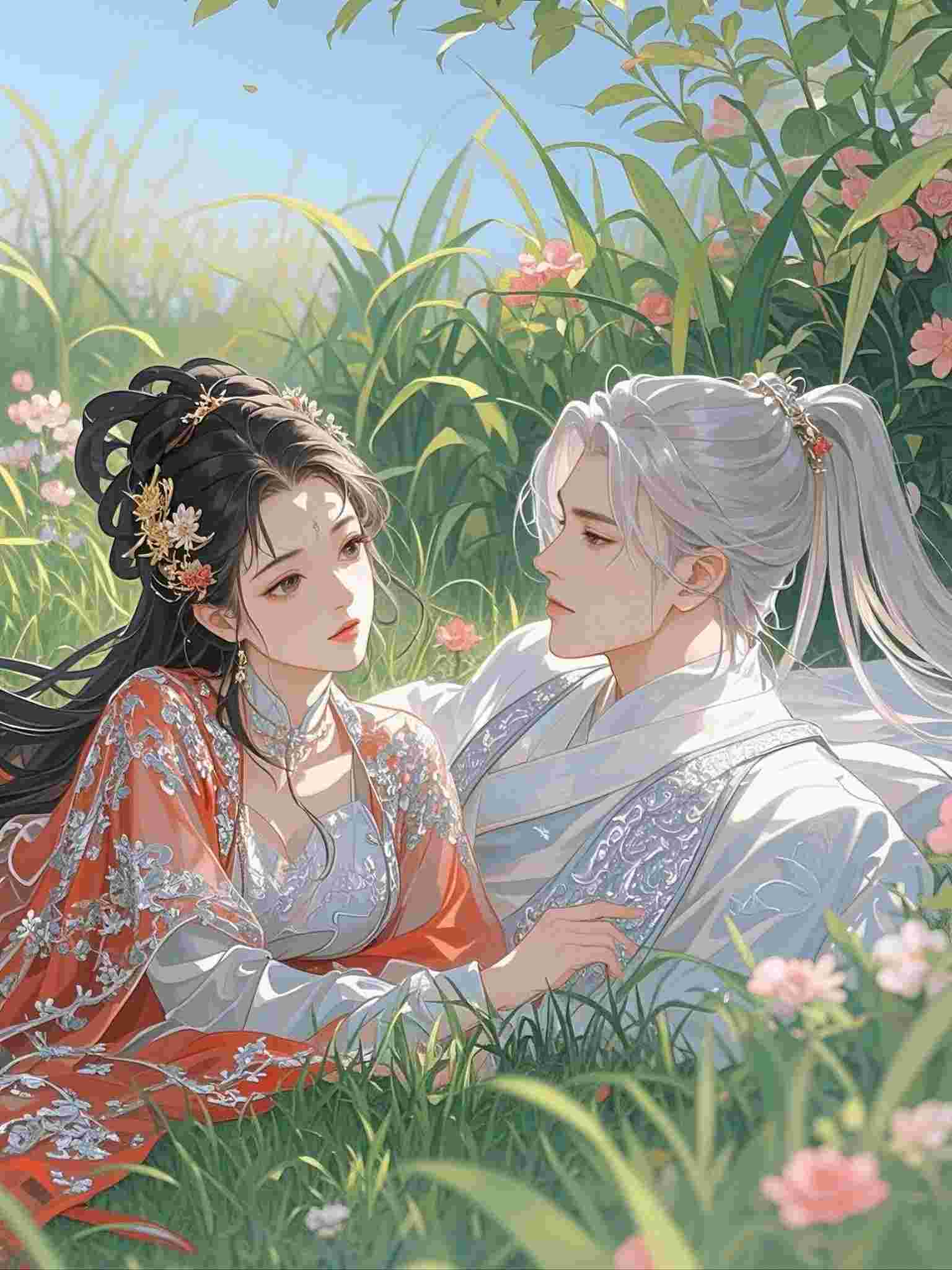
深渊之上无灯火全文无删减
推荐指数:10分
陈野沈知遥是现代言情《深渊之上无灯火全文无删减》中涉及到的灵魂人物,二人之间的情感纠葛看点十足,作者“狸三三”正在潜心更新后续情节中,梗概:陈野挂在九十米高的岩壁上,夕阳熔金般舔舐着他绷紧的肩胛骨。他皮肤黝黑,全身装备齐全,双手用力,双脚紧蹬,双眼凝视着前方。夕阳下,他眯着眼,望向夕阳的方向。突然松开一只手,朝下方挥了挥,像栖息在绝壁上的鹰。沈知遥站在观景台上,指甲陷进掌心。“下来,”她喃喃道,“求你了。”风声吞没了她的乞求。沈知遥第一......
第5章








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