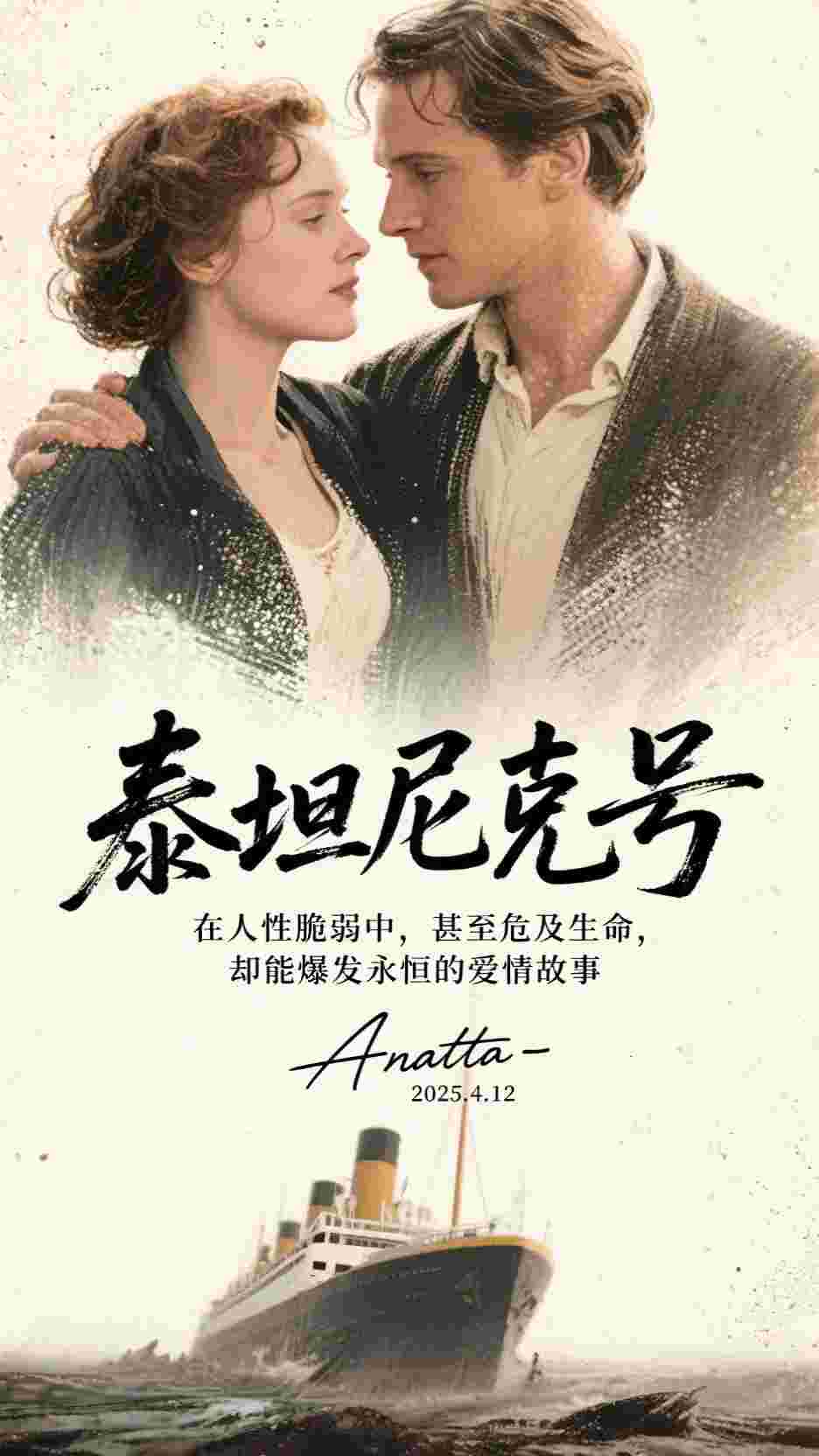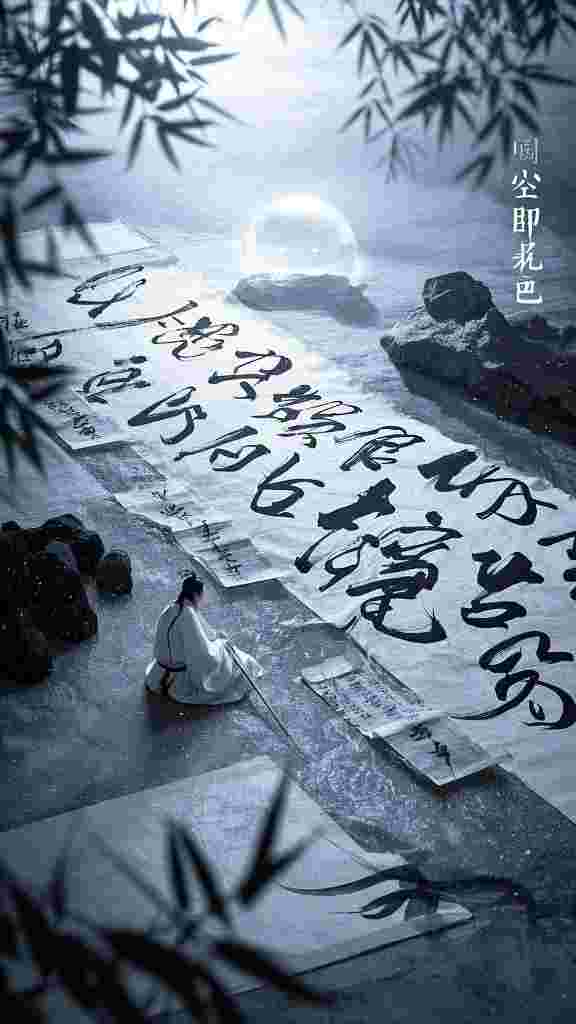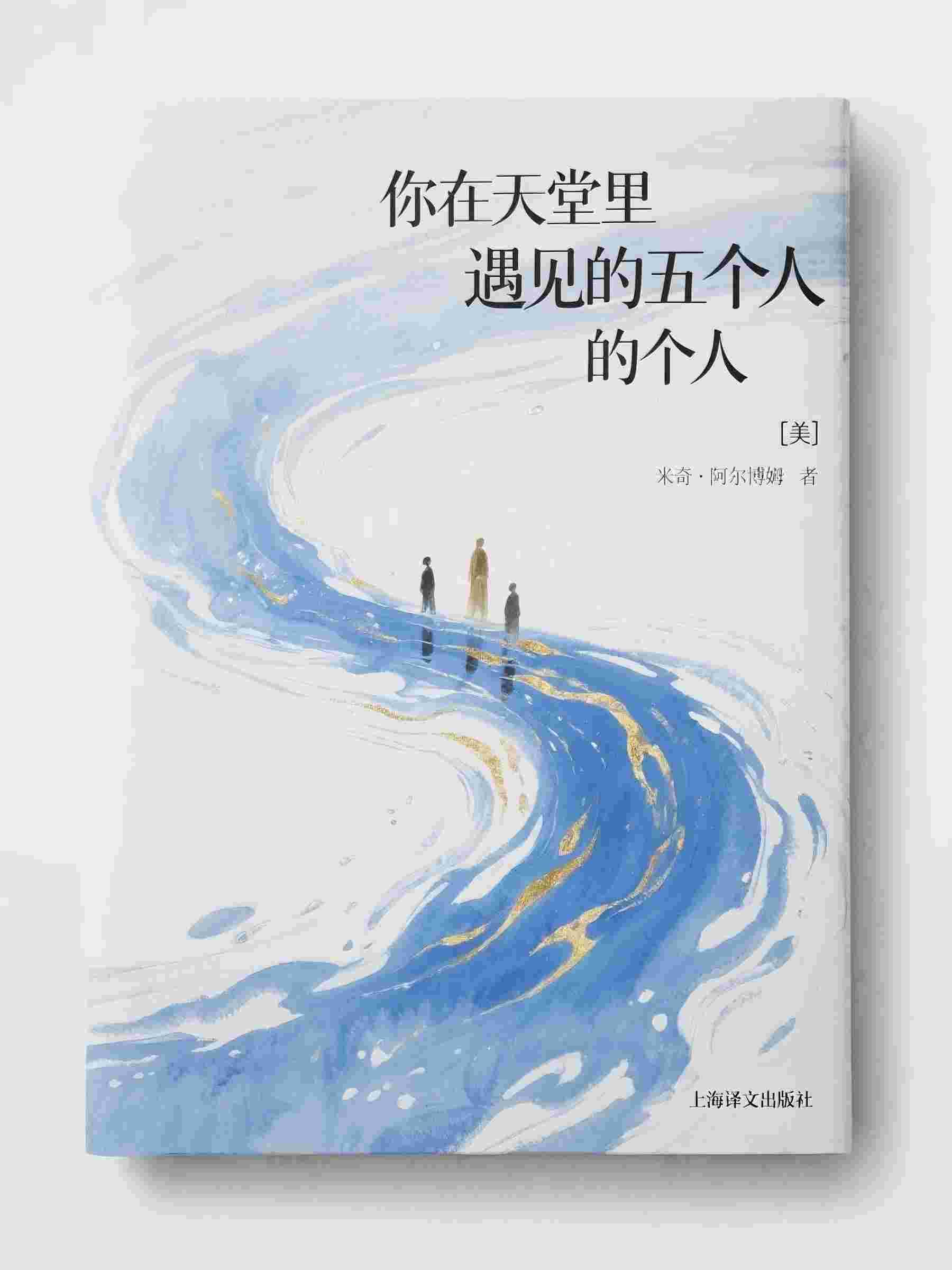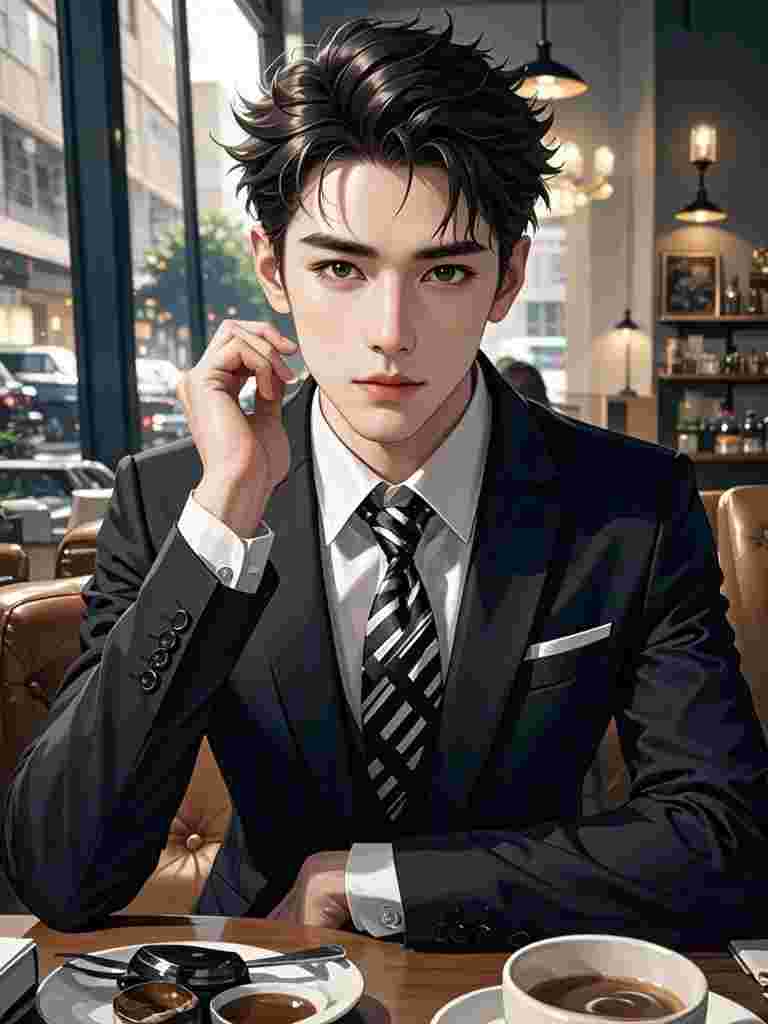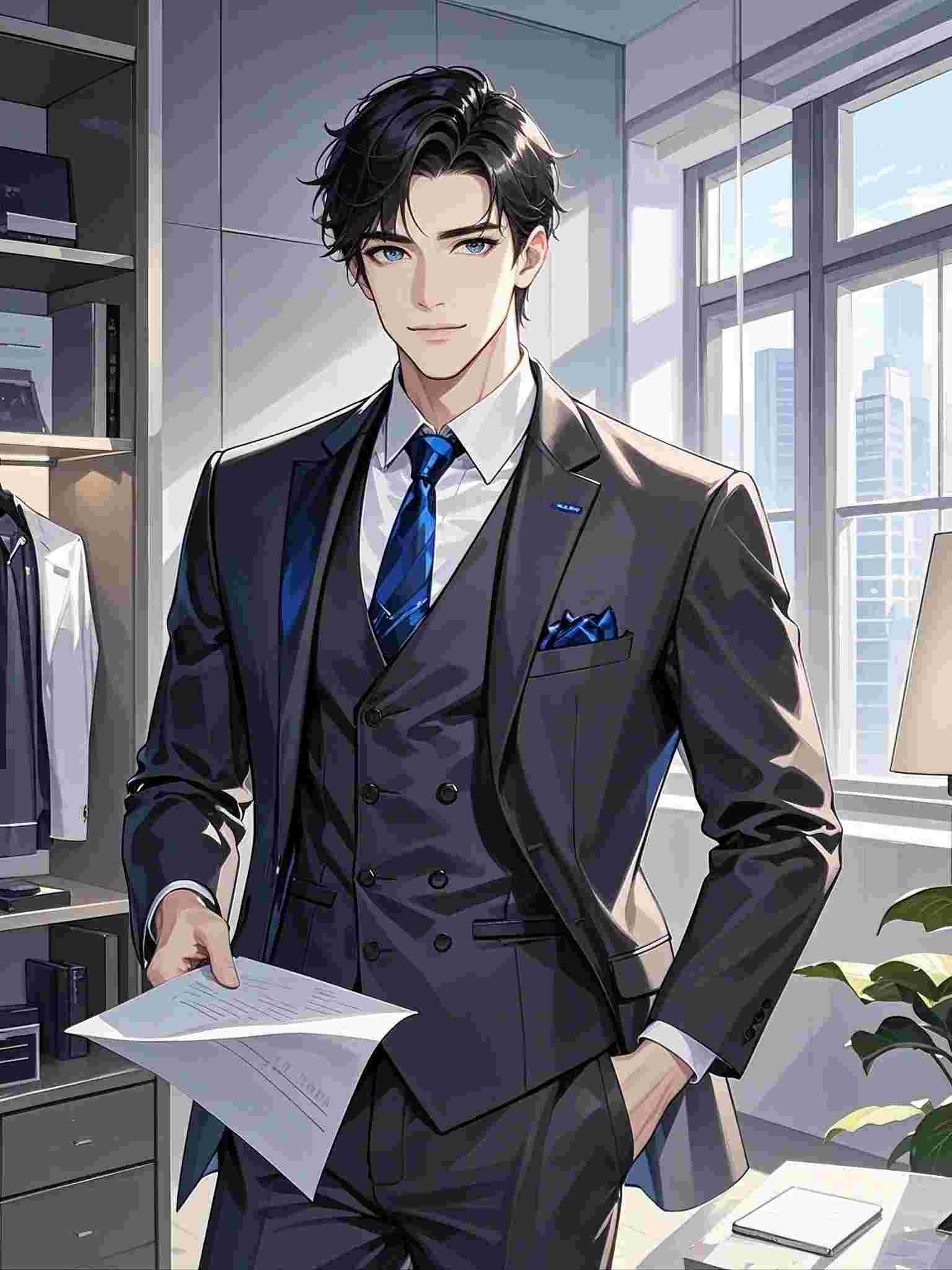;她把苏砚的书房改成了画室,墙上挂着她画的玉簪花——有春天的花苞,夏天的盛绽,秋天的凋零,冬天的枯枝,每一幅下面都写着一行小字:“致苏砚”。
她依旧在小学教美术,只是多了个习惯:每次带孩子们画画,都会教他们画玉簪花,会跟他们讲一个关于少年和玉簪花的故事。
孩子们总问:“林老师,那个少年后来回来了吗?”
她总是笑着摇头:“他没回来,但他一直住在玉簪花里,住在春天里。”
这天下午,她收到一个陌生的快递,寄件人地址是邻市的一家养老院。
她拆开快递,里面是一本泛黄的笔记本,封面上写着“苏父日记”。
笔记本里夹着一张纸条,是养老院护工写的:“林小姐,这是苏建国先生去世前托付我们寄给你的,他说这是他欠苏砚先生的,也是欠你的。”
苏建国,是苏砚的父亲。
林向晚只在照片上见过他——照片里的男人穿着中山装,笑容温和,抱着年幼的苏砚,背景是院子里的老槐树。
她一直以为苏砚的父亲是个普通的工人,却没想到笔记本里藏着另一段故事。
她坐在画室的藤椅上,翻开笔记本。
苏父的字迹很工整,带着年代感:“1998年,今天阿砚第一次见到向晚,那丫头穿着白裙子,像朵小玉簪花。
阿砚回来跟我说,他要娶这个丫头,我笑他傻,却偷偷在院子里种了棵槐树,想着等他们长大,就在槐树下办婚礼。”
“2005年,生意失败,欠了高利贷。
我不敢告诉阿砚,怕影响他高考。
今天催债的人来家里,砸了阿砚给向晚买的玉簪花苗,阿砚跟他们拼命,我却只能躲在房间里哭。
我对不起阿砚,对不起这个家。”
“2006年,我知道自己撑不下去了。
阿砚高考考得很好,能去北京的大学,可我不能让他带着债务去。
我跟向晚的父母谈了,我说我愿意去自首,让他们帮我还一部分债务,条件是让向晚去国外——我怕阿砚知道真相后,会为了还债放弃学业,更怕他耽误向晚的一生。”
“2006年夏,我写了这封信,却不敢给阿砚。
我怕他恨我,怕他知道是我逼走了向晚。
如果有一天,向晚能看到这本日记,希望她能原谅我,也希望她能知道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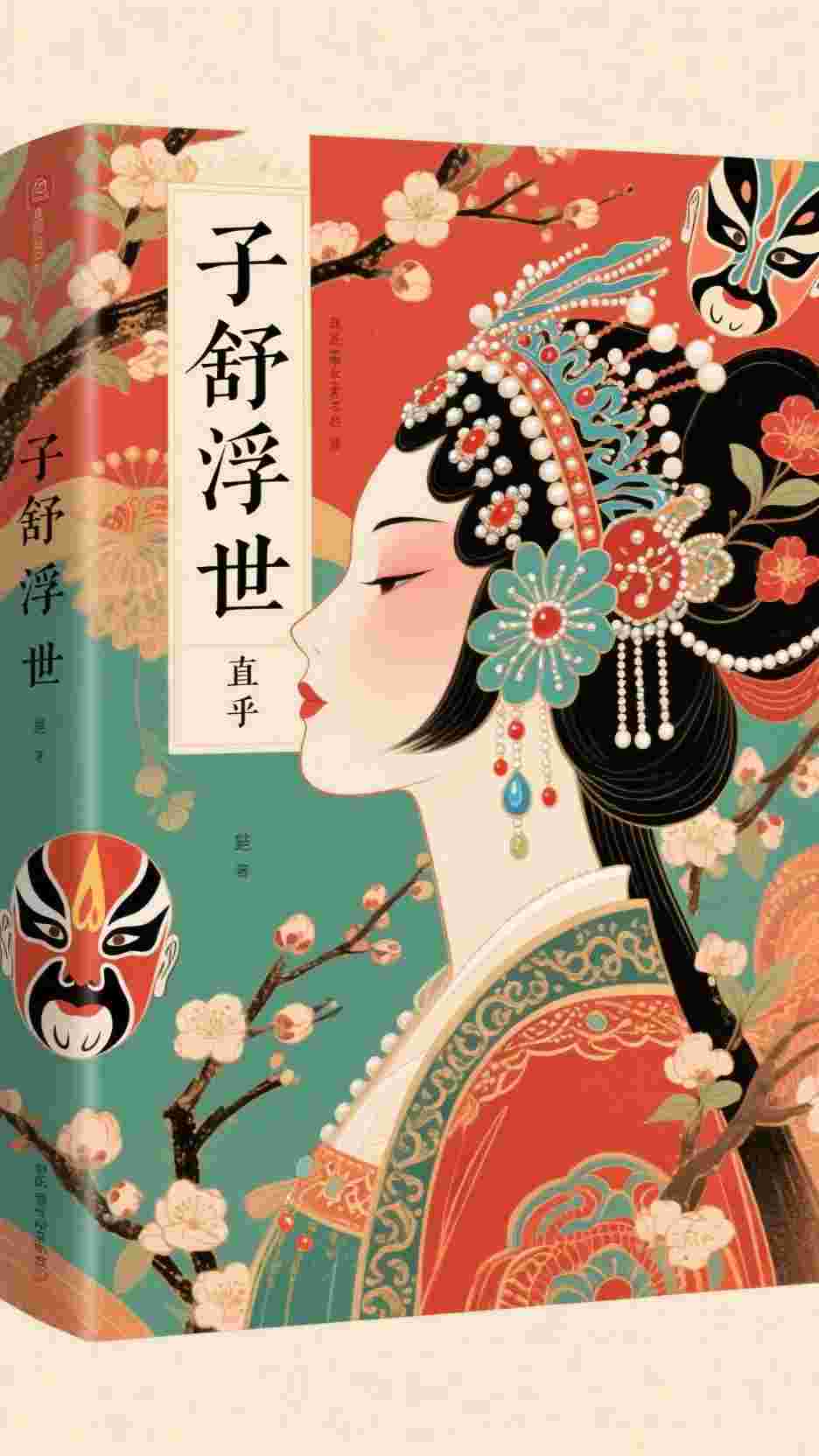
雨落向晚时苏砚林向晚全文+结局+番外
推荐指数:10分
以现代言情为叙事背景的小说《雨落向晚时苏砚林向晚全文+结局+番外》是很多网友在关注的一部言情佳作,“观山见越”大大创作,苏砚林向晚两位主人公之间的故事让人看后流连忘返,梗概:第一章 旧巷雨声林向晚再次回到这条巷弄时,是江南梅雨季的第七天。青石板路被雨水泡得发亮,倒映着两侧斑驳的白墙和歪斜的电线。她撑着一把黑色折叠伞,伞骨有些变形,风一吹就往一边歪,雨水顺着伞沿落在她米白色的风衣上,晕开深色的痕迹。巷口那家曾经卖桂花糖粥的小店早就关了,如今换成一家快递驿站,红色的招牌在灰......
第13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