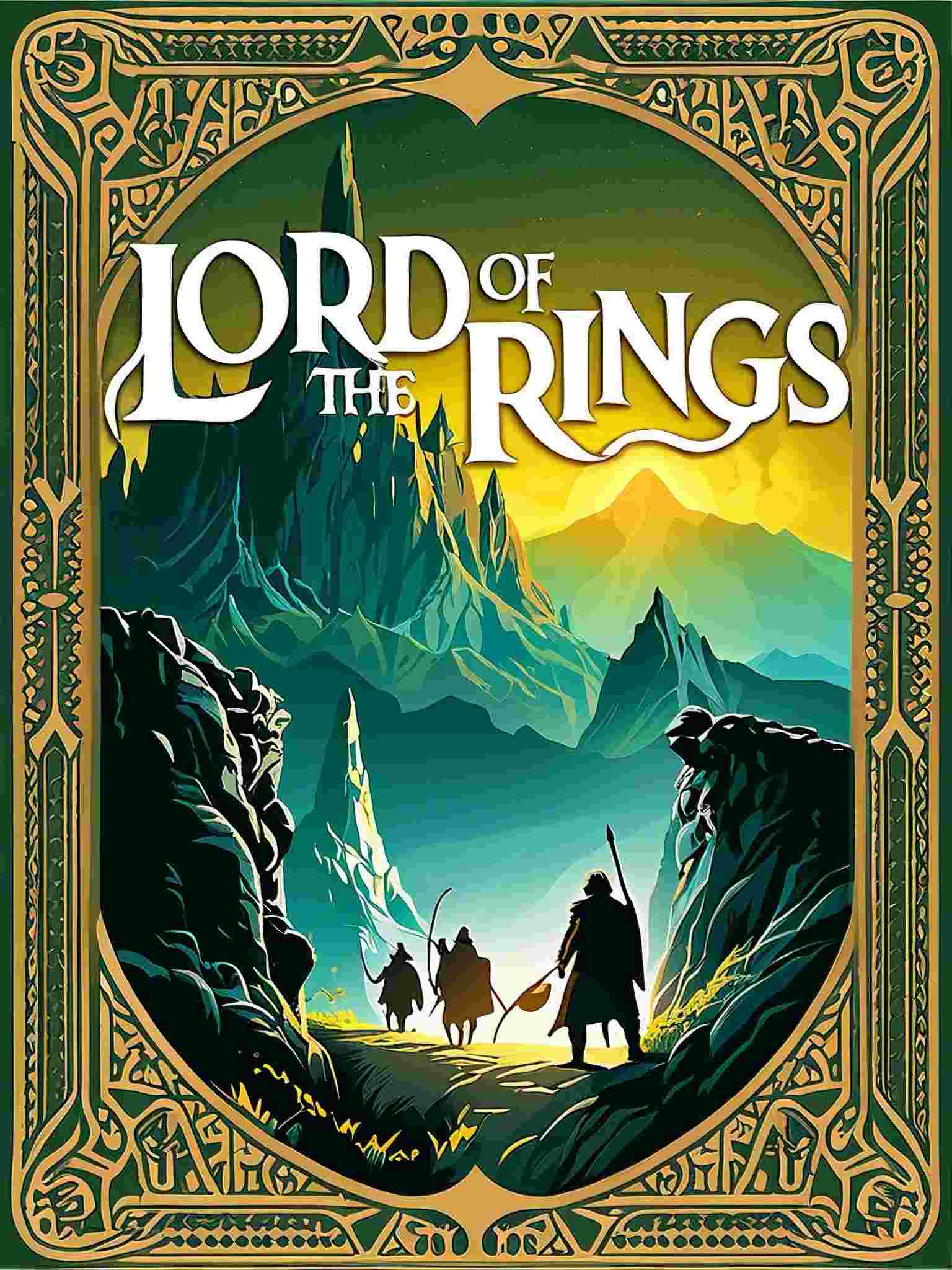妈抓住舅舅的肩膀用力摇晃,声音发颤。
建军舅舅被她摇得晃了晃,那直勾勾的眼神终于松动了一下,缓缓聚焦,落在了妈妈脸上。
一丝清醒回归,随即被巨大的恐惧淹没。
“姐……”舅舅“哇”一声哭了出来,猛地抱住妈妈,浑身抖得像秋风里的叶子,“他又来了!
那个白胡子老头!
就在屋里!
刚才就站在炕边地上看着我!
真的!
我看见他了!”
姥姥赶紧下炕,哆哆嗦嗦地又把煤油灯点亮了些,举着灯在炕前的地上来回照:“哪有啊,没有,儿子你看花眼了,做梦呢,吓着了……不是梦!
不是!”
建军舅舅把脸埋在妈妈怀里,哭得撕心裂肺,“我醒了!
我看见他了!
他就站在那里,穿着黑乎乎的衣裳,脸白的像纸,胡子那么长……他看着我,冲我笑……然后、然后他就要往炕上爬!”
最后这句话让妈妈的后颈子都凉了。
她紧紧抱着弟弟,一遍遍拍着他的背:“不怕不怕,姐在呢,姐在呢,啥也没有,你看错了……”话虽如此,但她自己的声音也在抖。
她死死盯着炕前那片被煤油灯和月光共同照亮的地面,心脏狂跳,生怕下一秒真有什么东西从阴影里浮现出来。
那一夜,舅舅再也没能安然入睡。
只要一合眼,不超过十分钟,必定会惊厥着醒来,哭喊着说看见白胡子老头站在地上看他,甚至有一次说老头已经坐到了炕沿上,正伸手要摸他的脚。
妈妈和姥姥也不敢睡了,就这么守着他,直到窗外天色发白,鸡叫头遍。
阳光逐渐驱散了黑暗,那种无所不在的阴冷恐惧才似乎稍稍减退了一些。
建军舅舅熬得眼睛通红,小脸煞白,下炕时腿都是软的。
姥姥忧心忡忡,天刚亮透就急忙又去请赵先生。
赵先生来得很快,听了描述,眉头锁得更紧了。
“白胡子老头?”
他捻着胡须,沉吟半晌,“埋的那外乡人是个壮年汉子,没留胡子啊……”这话让妈妈刚燃起的一点希望又破灭了。
“不是他?
那、那会是谁?
为啥缠着建军?”
赵先生摇摇头:“不好说。
撞客这东西,有时候不一定就是新死的鬼。
也可能是路过的游魂,或者…坟场里别的老东西,借着那外乡人的怨气出来了。”
他看了看吓得魂不守舍

舅舅的故事前文+后续
推荐指数:10分
无广告版本的现代言情《舅舅的故事前文+后续》,综合评价五颗星,主人公有秀兰热门,是作者“席之郎”独家出品的,小说简介:这是一个妈妈给我讲过的真实故事。一九七五年,秋收刚过,东北的夜晚来得特别早。天擦黑的时候,妈妈李莉就听见院门外有动静。她推开吱呀作响的木门,看见舅舅建军正蹲在门口的石墩上,脑袋耷拉着,手里攥着半块干硬的窝头。“姐,娘叫你去一趟。”舅舅抬起头,十五岁的舅舅脸上却有着不符年龄的愁容,“娘说...姥恐怕不......
第7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