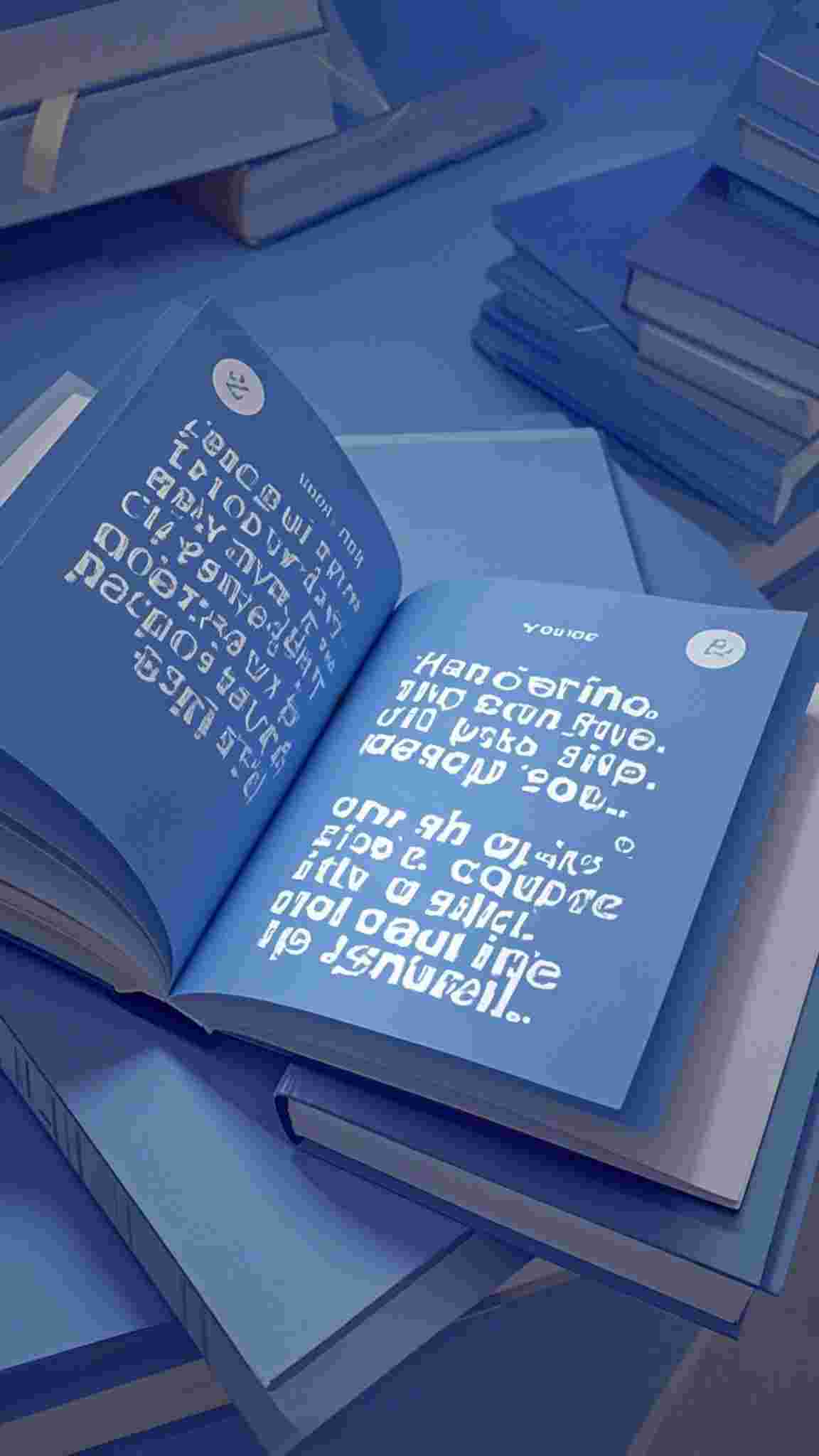,开玩笑问:“哇,你年轻时也追过星啊?”
姜柠接过书签,看着上面少年人青涩却已锋芒毕露的脸,笑了笑,语气平静:“是啊,那时候他很红。”
她将书签夹回一本不常翻看的乐理书里,动作自然,仿佛那真的只是一段无关紧要的青春记忆。
只有她自己知道,指尖触碰纸张的瞬间,那早已沉淀的心湖,还是被投下了一颗微小却沉重的石子,荡开无声的涟漪。
他们早已接受了命运的安排,在各自的人生轨道上运行得平稳甚至优秀。
他们不再有执念,不再有幻想,理性早已将过往归档封存。
可是,那些猝不及防的瞬间——一种味道,一段旋律,一个似曾相识的和弦错误,一张泛黄的旧书签——却像狡猾的刺客,总能精准地绕过所有理智的防御,刺中那颗被时间层层包裹、以为早已不再疼痛的心。
疼得不尖锐,不撕心裂肺,只是一种沉闷的、绵长的钝痛。
像阴雨天气里发作的旧伤,提醒着那里曾有过怎样一场惊心动魄的断裂。
然后,那感觉会慢慢淡去,被眼前的孩子、工作、家务、下一项日程覆盖。
他们继续生活,一如既往。
他们不再流泪,只是偶尔,在无人知晓的刹那,会感到一种深入骨髓的疲惫和怅惘。
仿佛一生中最好的部分,最真实的情感,早已在那个为了所谓“正确道路”而转身的选择里,消耗殆尽。
余下的,不过是得体而漫长的,余震。
时间的河流平缓地向前,水面之下却沉着无法冲散的沙金。
转眼又是三年。
宋亚轩推掉了一部大制作电影的男一号邀请,理由是想“沉淀一下”。
他在市郊的工作室弄了个小小的录音棚,不对外营业,只偶尔接待几位多年老友,一起玩些不打算发行的音乐。
外界评论他“半隐退”,粉丝虽遗憾却也尊重。
他的生活节奏变得更慢,像一首从激昂副歌过渡到舒缓间奏的歌。
姜柠的生活同样沿着既定的轨道平稳运行。
她的音乐治疗工作室在本地小有名气,孩子上了小学,日子被学校的活动、患者的课程和家庭的琐事填满,充实得几乎没有缝隙。
她很少再想起国内娱乐圈的纷扰,那段顶着星光也踩着刀尖的日子,遥远得像上辈子的事。
然而,那些

三秒月光宋亚轩姜柠前文+后续
推荐指数:10分
小说《三秒月光宋亚轩姜柠前文+后续》,此书充满了励志精神,主要人物分别是宋亚轩姜柠,也是实力派作者“小小屁啊哦”执笔书写的。简介如下:设定· 顶流偶像生态:严格禁止恋爱的行业规则,粉丝经济下的情感商品化· 双重生活困境:台上阳光偶像与台下压抑自我的割裂感· 音乐作为隐喻:用欢快旋律包裹悲伤歌词,象征外表与内心的矛盾· 心动契机:宋亚轩发现音乐助理姜柠总能精准理解他想要的音乐情绪· 甜蜜煎熬:创作中的亲密默契与工作外的刻意疏离形成强......
第7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