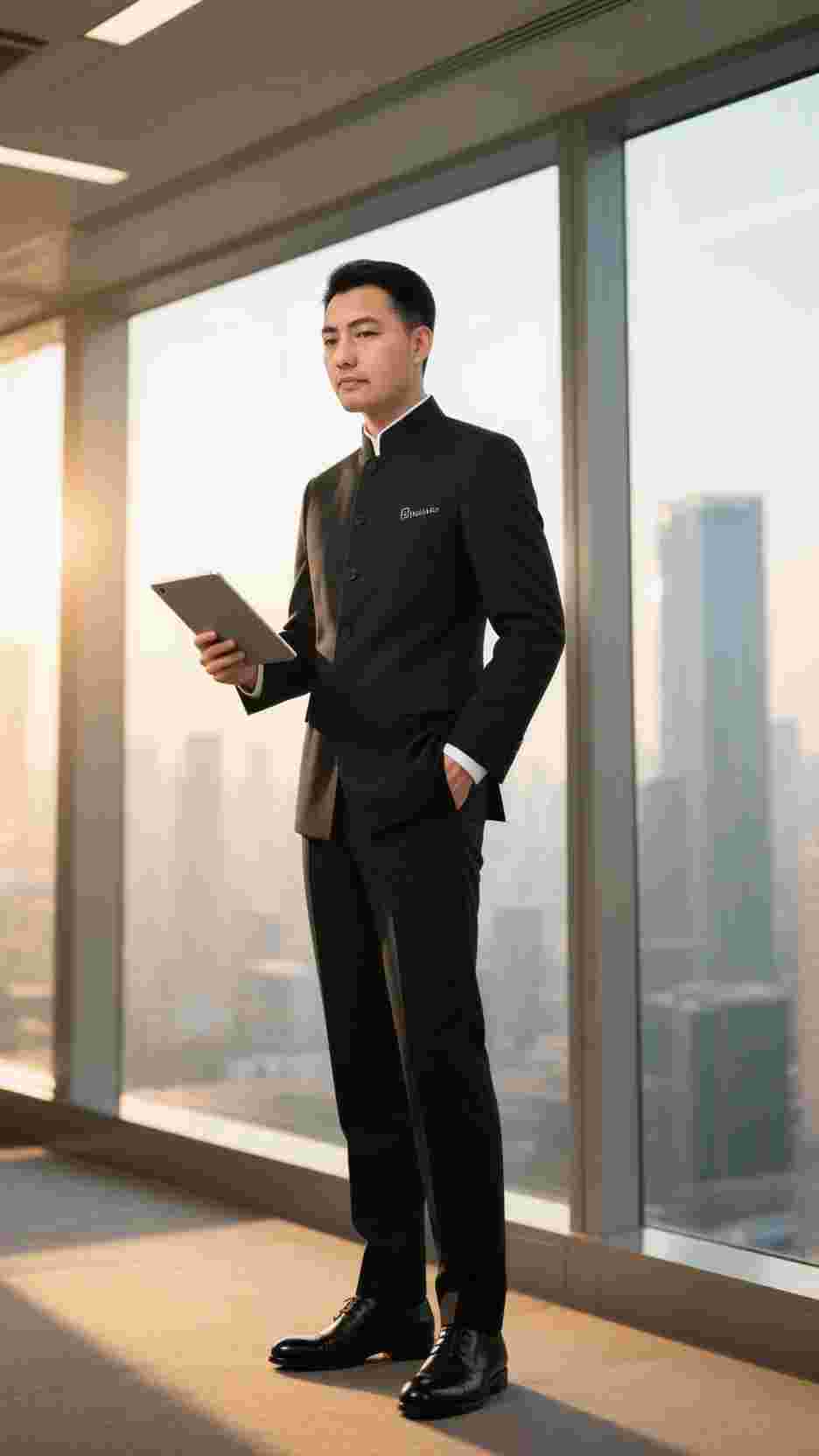营里的金疮药,回来时却看见将军扶着墙,用牙齿咬开布条,自己换药。
他疼得浑身发抖,却不肯出声。
我冲过去,一把抢过药瓶,手指沾了药粉,抖得撒了他一身。
他捉住我的手腕,在我掌心写: “别怕。”
我眼眶发热,却倔强地别过头。
指尖在他掌心回写:“疼就说。”
他笑了笑,写:“疼才记得。”
腊尽春回,雪开始化。
破庙的屋檐滴答滴答,像谁在数日子。
将军的左手练得能写一整页字,字迹瘦劲,像雪压不折的竹。
他给我写的第一页是: “谢氏家训第三条:欠债还钱,欠命偿命。”
我回:“柳怀恩的命,我来收。”
他看着我,眼底有雪光闪动,写: “不,是我们。”
那天夜里,我第一次听见将军的笑声。
极轻,像雪落在剑锋上。
他左手执笔,在破纸上画了一张图——柳怀恩的营帐分布、巡逻路线、换岗时辰。
我凑过去看,鼻尖几乎碰到他下巴。
他忽然抬手,在我发顶揉了揉,像揉一只冻僵的雀。
我僵住。
他在我掌心写:“阿九,等春天到了,我带你回家。”
我低头,写:“家早没了。”
他回:“那就再造一个。”
雪化尽那日,将军能自己走路了。
我们站在河边,冰面裂成千万片,水声轰鸣。
他弯腰,捧起一抔雪,捏成拳头大小,递给我。
“像不像元宵?”
他写。
我点头。
他忽然伸手,把雪团按在我眉心。
冰得我一哆嗦,他却笑弯了眼。
那一刻,我忘了柳怀恩,忘了血债,忘了十年前的火海。
只记得雪团在眉心化开,像一滴迟到的泪。
夜里,我们躺在稻草上,听春雷滚滚。
将军的手指在我掌心一笔一划,写得很慢,像要把每个字刻进骨头: “阿九,我若死了,别回头。”
我翻身压住他的手腕,写: “你死,我跟着。”
他看着我,眼底有雪崩。
半晌,写:“傻子。”
我写:“你教的。”
春雷过后,雨来了。
破庙漏雨,滴滴答答落在将军的右手上。
我撕了衣角给他遮,他却摇头,用左手握着我的手,写: “让它疼,疼才记得。”
雨声里,我忽然明白—— 我们像两柄被雪埋住的刀,互相磨砺,互相取暖,只等春雷一响,就要见血。
雨停那日,将军在破庙的

我是哑巴校尉,将军他夜夜求偿谢无衣谢侯:(番外)+(结局)
推荐指数:10分
书荒的小伙伴们看过来!这里有一本“微辣是我最后的妥协”创作的《我是哑巴校尉,将军他夜夜求偿谢无衣谢侯:(番外)+(结局)》小说等着你们呢!本书的精彩内容:雪落无声,却压断了枯枝。我蹲在灶门口,把最后一根松枝塞进炉膛,火苗“哔剥”一声窜起,舔红了半边墙。火光映着我的影子,像一条匍匐在地的狼。“阿九,汤好了吗?”帘外有人咳,声音不大,却压得四座皆静。那是将军的声音,哑得像砂纸磨剑。我把汤舀进粗瓷碗,碗沿烫手,我却不觉得——五根手指早被北疆的冬天磨得只剩茧......
第4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