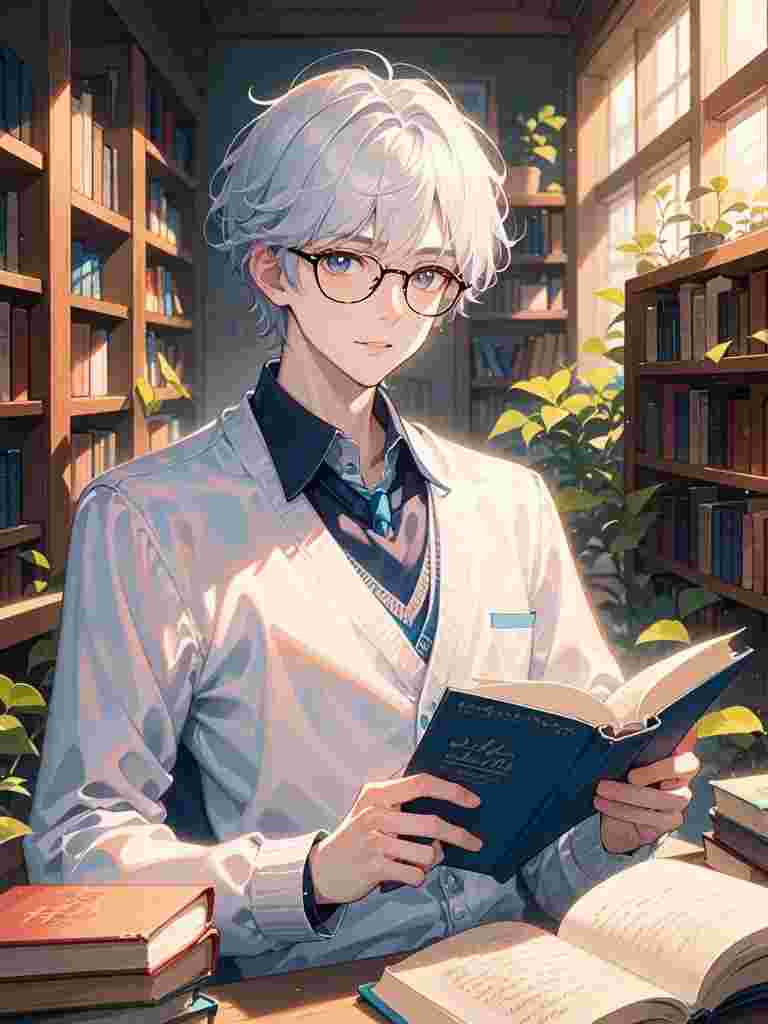他下半辈子安生。
他走了。
我继续往主峰走。
青霄门今日召开问心台大会,议的是“外敌渗透”之事。
裴无咎亲自提议的。
他坐在高座旁侧,穿月白长衫,袖口绣银线云纹,像极了当年刚入门时的模样。
那时他低头说话,声音轻得像怕惊了人。
守台弟子拦在石阶前。
“弃徒不得登台。”
我从怀中取出那半截断剑,剑柄朝上,刻着一个“归”字。
这剑是我在刑律堂留下的,现在由我亲手拿回来。
守台人盯着剑柄,喉结动了动,侧身让开。
石阶共九十九级,我一步步上去。
风从背后吹来,墨袍掀动,玄铁软甲压着肩。
台上长老坐着三人,两左一右,中间那位须发皆白,是刑律堂出身的陆长老。
他看见我,眉头一跳。
裴无咎站起身,拱手:“师兄怎也来了?
今日议事,不涉私怨。”
我走到台心,离他五步远。
“私怨?”
我开口,声音不大,但整个问心台都听得清,“你给北燕写的信,落款没署名,只按了指印。
你右手拇指第二道纹偏左,小时候练剑压出来的。
这指印,我认得。”
他脸色没变,但左手微微收拢。
台下已有骚动。
我从剑鞘夹层抽出那封信,抖开,朗声道:“寅七桩已立,青霄为基,雪夜举火,九派可倾。”
声音落定,台下一片死寂。
裴无咎笑了:“好一出苦肉计。
你被逐出门,心怀不甘,竟伪造密信污我清白。
可有证据?”
话音未落,他抬手一扬,一张纸飘向陆长老:“这是他在边城与北燕细作往来的凭证,上有他亲笔签名。”
陆长老接过一看,皱眉。
我冷笑:“你伪造的墨色带铁腥气,是北地贡墨。
你忘了,我师父写字用松烟,而你抄我师父笔迹时,连纸都换成了漠南官坊产的薄笺。”
我伸手入怀,取出拼合的玉符,甩手掷向案前。
“这是北燕七号密桩信物。
你若与此无关,为何昨夜刑律堂通风口被钉死?
为何焦灰里有《九派布防录》残页?
为何陈砚的名字被朱笔划掉,却没死?”
陆长老拾起玉符翻看,忽然抬头:“这狼头火漆……与北燕军符一致。”
裴无咎终于变了脸色。
他猛地抽出佩剑,直刺我心口。
我侧身避过,剑锋擦过肩甲,火星一闪。
他连攻三剑,招式凌厉,最后

妻子逼我把功法给师弟后,她悔了萧沉舟沈清璃无删减全文
推荐指数:10分
《妻子逼我把功法给师弟后,她悔了萧沉舟沈清璃无删减全文》中的人物萧沉舟沈清璃拥有超高的人气,收获不少粉丝。作为一部现代言情,“桃子快到怀里来”创作的内容还是有趣的,不做作,以下是《妻子逼我把功法给师弟后,她悔了萧沉舟沈清璃无删减全文》内容概括:我叫萧沉舟。青霄门大弟子。娶了掌门独女沈清璃。本以为一生顺遂。可她看小师弟的眼神,像在看光。而我,只是她身边的影子。他叫裴无咎,来门派才三个月。温柔谦卑,人见人爱。可她为他,拿剑指着我。要我交出残卷功法。我笑了,递上秘籍。心,却碎成了灰。三年夫妻情,抵不过一个外人。我写下和离书。转身离开剑阁山。江湖......
第13章